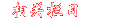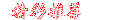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北京汇文中学“贺龙班”成立 全国招生贯通化、一体化培养田径人(02月23日)
- 怀念一位百岁晋绥老前辈(01月27日)
- 家中吊唁蹇阿姨……(01月03日)
- 他是最后一位亲历者(11月28日)
- 永远和老区人民在一起(09月09日)
- 基金会七年资助2918名寒门学子圆梦大学(09月07日)
- 岢岚县举行“2022晋绥情·阳光助学公益活动”捐助仪式(09月02日)
- 临县“2022晋绥情·阳光助学公益活动”捐助仪式举行(08月29日)
- 保德县“2022晋绥情·阳光助学公益活动”捐助仪式举行(08月26日)
- 石楼县“2022晋绥情·阳光助学公益活动”捐助仪式举行(08月26日)
我随父亲“占领”日本
发布日期:2017-09-19 11:19 来源: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作者:廖品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投降后应由盟国派遣占领军,在日本要地实行占领,以监督其解除武装(只保留警察武装)和降书的具体实施。美国以盟国总司令国名义,多次要求中国向日本派驻占领军。后经民国政府决定,向日本派遣由荣誉第一师、二师组成的第67师,以戴坚少将为师长,作为盟军占领军中国派遣军开赴日本。家父廖季威奉命以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队上校参谋身份飞赴日本协调处理先遣事宜。后来占领军未能成行,仅派出代表团。我父亲曾感叹:‘我是抱憾终生的中国占领军上校。’
家父于1932年18岁时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兵,1936年毕业归国。在南京步兵学校任学兵连长区队长,武汉会战时为炮兵51团营长。因家父精通日语,1940年调到军令部担任参谋,从事对日情报研究工作。在重庆期间,父亲与宋楚瑜的父亲宋达是同事,宋达亦为上校参谋,与我母亲苏荣辉又系湖南同乡,两家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我随家父第一批还都南京,随又同父亲迁往上海。1946年5月家父奉命随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戴坚等飞赴日本,协调中国驻日占领军先前事宜。后因国内国际局势变化内战爆发,第67师转为内战部队,赴日计划取消,家父和其他先遣官转入中国驻日代表团,家父为代表团军事组成员。当时规定代表团校级以上官员可带家属,我便于当年11月随母亲和其他代表团家属一起飞赴日本。下面是我当年赴日前后的一些见闻:
第一次见到日本兵可恨又可怜
我第一次见到日本兵,是在国内。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父亲还都南京后,我家住在玄武湖边一个兵营里。兵营里面有不少等待遣返的日本军人。我亲眼见到他们10个人一组围着一个大菜盆吃白米饭。
这些日本兵有时被中国士兵看押着出营地拉米、拉菜什么的。这是他们很害怕的差事。因为只要一出营地,就难免遭受对日本兵恨之入骨的南京市民围殴。由于看押士兵也痛恨侵略者,往往对民众围殴睁只眼闭只眼。挨打的日本兵,一则已奉命不许还手,一则也深知对不起中国人,因此即便被市民打得鼻青脸肿都绝不还手,甚至也不躲避。现在想来,这些日本兵真可怜,但是,比起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实在又太便宜这些惨无人道的侵略者了。
登上父亲乘坐的赴日轰炸机
家父于1946年5月27日与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顾问李立柏少将及四名文职人员,占领军戴坚少将、副官王上尉、名古屋港口司令卢东阁海军中校等九人,一同从上海江湾军用机场飞赴日本。为显示战胜国的威武,安排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队一行乘坐美制B24轰炸机飞赴日本。B24四发远程重型轰炸机。该次飞行没带炸弹,保留了十几挺机关炮。
当天,时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祯等大批军政要员、媒体及家属前往送行。我和一些家属还被机组人员带上飞机参观,还进驾驶舱参观了机关炮。我后来从《飞向光明》一文中获悉到,执行这次飞行任务的是空军第八大队,机长是刘善本先生,他日后驾机起义。
飞机于中国时间上午9时起飞,日本时间下午4点多降落于日本厚木机场。这是一个军用机场,当年麦克阿瑟从菲律宾飞抵日本,也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这是当时日本极少数能降落大型飞机的机场之一。
代表团取道横滨前往东京,父亲和占领军人员,在横滨工作。当年7月上旬,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突然接到国内消息,占领军因故取消,我父亲转为驻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
飞日途中与冰心母女座位比邻
由于民国政府做出代表团校级以上官员可以带家属到日本的规定,1946年11月……日,我随母亲一起,跟其他代表团官员的亲属飞赴日本。
我们乘坐的是C47军用运输机。由于人多座位少,小孩没座位,我由母亲带着。坐在我们旁边的是冰心和她小女儿吴宗黎(后改名吴青)(吴宗黎的姐姐和哥哥是后来去日本的。)我在飞机上就跟吴宗黎熟悉了。她比我大一岁,很活泼大方,我们在飞机上就成了玩伴。我们这趟飞机也是在日本厚木机场降落的
2014年,我和吴青还受邀一同接受多种媒体的采访。
原日本林业省成为代表团驻地
到了日本,抵达东京麻布区的中国驻日代表团驻区。中国驻日代表团驻区包括办公区、礼堂、团长官邸、校级以上官员官邸、励志社、迎宾馆等部分。
其中,办公楼是一个三层的楼房,据说曾是日本林业省办公楼。代表团在楼上设了电台,这是与国内联系的主要工具。办公楼前有个操场,有一个旗杆,宪兵每天进行升旗、降旗仪式和换岗。
励志社在办公楼对面,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楼上单身代表宿舍。励志社一楼住着40个宪兵,他们是从远征军宪兵二营抽调的一个加强排。宪兵们住在一个大屋里,一人一个白木床,单层的。当时20个日本警察配备一把手枪,中国宪兵则是每人配备一把德制盒子枪。宪兵的营房内还要两挺捷克轻机枪,我和小朋友们曾去玩弄过。励志社后边有一个集体食堂。周末的时候,把餐桌搬到一边,在地上撒上滑石粉,就成为舞厅。当时,那里还配有日本服务员,负责买菜、为宪兵们扫地、搽皮鞋等。
迎宾馆在励志社东北,隔一条街。迎宾馆是一排木纸结构的平房。网上看到一张冰心家的照片,标注为冰心在日本的寓所前留影,其实那个背景是迎宾馆。冰心家在迎宾馆旁边。
迎宾馆北边是代表团军事组空军中校雷炎均家。雷炎均曾在抗战中击落日本根井航空队队长的座机。他到日本后曾前往看望昔日战场对手的家属,还给过生活困难家庭一些资助。他本人日后去台湾,官至空军司令,上将衔。
与王丕丞家比邻
当时中国驻日代表团的门牌号是按中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英文缩写编的。我家的门牌号是CMD11。这是一个两层楼的日式别墅,进门有一个院子,楼房是落地玻璃的平推门,每层有8间房。我家住在一楼。原张学良先生机要秘书、代表团政治组的苗剑秋先生家住二楼。
我家旁边的CMD12号是军事组长王丕丞少将家。他家有四个孩子,老大在国内当空军,去日本的有三个,其中老三王太三跟我同年。王丕丞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先后就读于德国工兵学校、英国皇家参谋学院,当过驻苏联和法国武官,面见过斯大林、丘吉尔、希特勒等很多二战领袖人物。他的二夫人曾在驻苏使馆工作,会英语和俄语,我母亲常和她一起逛街买菜。王丕丞将军经手了数以亿美元计军火物资交易,但在我印象中却是非常清廉的,他生活简朴,家里没有多少饰物,只是珍藏了几把日本军刀。王将军后来去了台湾,但官运不太好,直到60年代才象征性提升为中将。
佩戴盟军护照 享受特殊待遇
代表团成员在日本的待遇,比盟军低不少,但却比国内高不少。家父这个级别的官员,当时每人每月薪金600美金。这个标准高于国内将官。夫人待遇是丈夫的一半,小孩每人按父亲的四分之一发放。当时,国内使用法币,并且贬值严重,这就显得我们的待遇更高了。
当时日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市面上甚至没有零食卖。我们的食品每周由后勤处派车送到家来,是吃不完的。我们还能在盟军超市购买到很多市面上买不到的生活用品。
另外,代表团每周三晚上都要礼堂放电影。影片主要是国产片和美国的战争片,我还记得在那里看了《万家灯火》。
当时我们家还配有洗衣机和电冰箱。由于刚开始不太会用,第一次用它洗衣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螺丝钉,把衣服搅坏了,以后就用得比较少。
驻日代表团所有人,连同小孩都有盟军发放的护照。持有盟军护照,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公共汽车、看电影等特殊待遇,我们一些小朋友常到附近的盟军俱乐部去看电影和游泳。
我印象中,家里小孩最多的是后勤处长吴冠群家。他家有六个孩子,吴邵祯、吴邵祺、吴贵芳、吴美芳都是我当时很要好的伙伴。还有一个美国准将的小孩比尔,也常和我们一起玩耍,我们汉语、英语、日语、手势混用着跟他交流。
乘盟军牌照吉普到日本各地旅游 把彩色胶卷邮寄到美国冲印
驻日代表团组长以上文武官员都配有轿车,其他团员也有不少车辆。其中,代表团团长商震上将的坐骑是一辆别克轿车,车子没有车牌号,只是红底牌照上有三个金星,代表三星上将。王丕丞少将的是一辆福特车,牌照也是红底无号,一颗星。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也是这种红底无号车牌,不过他的牌照上是五颗星。这种车牌在日本享有很高特权,不仅日本警察,就是美国宪兵,沿途见到也要立正敬礼。
我父亲和一般官员的车牌都是有编号的盟军牌照。家父开一辆车门和车蓬都完好的美吉普,常在周末带我们去日本名胜景区游玩。京都、奈良、江之岛、日光山、海边等等我去过。
摄影是家父平生唯一嗜好,我现在的摄影爱好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在东京时,我们家有四架照相机,记得其中一架是135的德国莱卡,一架是日产双镜头玛米亚。父亲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彩色胶卷了。那时,日本还不能冲彩色胶卷,得邮寄到美国去冲印后再邮寄回来。我的小伙伴们刚看到冲洗出来的彩色照片,都很好奇,看到神奇怪异的彩色胶卷底片,更是兴奋。
我们在日本拍的很多照片,包括与冰心家的合影、战后日本风景等,都带回国了。但文革期间我家被四次查抄,有所当时的照片和珍贵史料都被抄没了,实在令人痛惜。
战后日本见闻
我到日本时,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但由于遭受多次轰炸,每次轰炸都是上百架B29轰炸机,每架次20吨炸弹,使得东京市区多年之后仍然还是满目疮痍。我印象很深的是,断垣残壁中常常能看到一些基本完好的铁质保险柜,成为整个废墟中唯一没有被毁坏的东西,显得格外醒目。
父亲生前回忆文章中提到,在46年广岛原子弹轰炸一周年纪念日,美国组织盟军前往爆炸点参观,他亲眼目睹爆炸现场的残留惨状,并向当地小贩买了几块因高温所致水泥、钢筋、玻璃熔合物作为纪念,我曾亲眼见过它们。
就我见闻和父亲回忆,当时日本的情况非常贫困。每人每天只有4两粮食。由于布料短缺,日本成人大多穿着拔掉领章的军装。学生校服则是黑色校服。盟军士兵在接上扔下一个烟屁股,立即有日本人抢着去拣。我的印象是,当时的日本情况,比我国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还要艰苦。
战后日本社会严重男女比例失调,这从街上的行人性别就能明显看出。那些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遣返的日本战俘,即使是伤残的,也不愁没女人嫁给他。
跟日本小孩群殴 到日本神社捣乱
刚到日本不久,我和别家的小朋友们都没有上学,大家一起玩耍,很快就相互熟悉了。当时旷日持久的日本侵华战争刚结束不久,加上我和几乎所有驻日代表团的家属都有躲避日军轰炸的痛苦记忆,还有不少人目睹过亲友在战争中伤亡的惨状。听母亲讲,我刚出生不久,日军轰炸成都,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和婆婆一起在成都跑警报,历经辛苦疏散到石板滩、新都等地躲避。因此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无不痛恨日本。初到日本不久,我们遇到日本小朋友时,常主动挑衅,跟他们打架斗殴。记得有一次斗殴打大了,日本小孩搬来日本警察助战,换岗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宪兵刚好路过,我们也跑过去搬救兵。宪兵听到我们告状,以为日本警察欺负我们,勃然大怒,纷纷拔枪示威,日本警察赶紧把日本小孩驱散,向宪兵和我们连声道歉。
为报仇雪恨,我们一群小朋友还到处用粉笔写抗日标语,包括在日本小学和警察局的围墙上写“打到日本鬼子”。我们有时还偷偷跑到驻地附近一个日本神社去捣乱。神社里有香案,供着不知名的日本菩萨,还有一个石头的水池。我们见有日本人神秘兮兮地舀里面的神水喝,就偷偷向水池里啊尿,看到日本人一本正经如痴如醉地豪饮做过手脚的神水,就躲在一旁偷笑不已。
在东京升起中国国旗
过了一段时间,有家长把几个中国小朋友送到驻地附近那个日本小学去读书。这几个小孩立即被其他小朋友骂为汉奸,受到孤立。由于日本小学用日语上课,这几个中国小朋友听不懂,又不受日本学生亲善,很快就拒不再去日本学校读书了,重新回到中国小朋友中来。
我到日本后大约半年左右,家长们的要求下,在冰心的努力和关怀下创办了一个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子弟学校。由两位老师教学当时国内的同年级课程,课程包括国语、英语、算术、图画、音乐、体育等课程。其中一个老师是代表团成员的夫人,她在国内本是教师。30多个小孩分成3个年级。我直接上的二年级。同班同学有张衍玲、王镇东、吴小农、王太三等,吴宗黎、张衍华比我高一级。
子弟校就在日本小学附近,老师和我们小朋友看到日本小学升国旗,就提出在子弟校树立一个中华民国国旗,并要求我们学校的国旗要比日本小学的国旗大、旗杆要高,因为我们是战胜国。国旗由学生们轮流升起,我也亲自升过好多次。每次升起国旗或者从我家看到子弟校的青天白日旗在东京上空高高飘扬时,我都感到无比自豪。
学校成立之初,我们还不时跟旁边的日本学生打架斗殴,后来两校老师商量,决定错开两个学校的放学时间,让日本学生稍微先放学,我们稍微推迟放学,以减少摩擦。
冰心校长为我们过4月4日儿童节
子弟校校长是吴文藻的夫人谢冰心女士,也就是著名的作家、儿童教育家冰心女士,我当时叫她吴伯母。冰心那时没负责教学,不常在学校,但特意为我们过了1947、1948年的儿童节。当时的儿童节定在4月4日。记得有一个儿童节给我们发了冰激凌、糖果。那时候冰激凌还很稀奇,小朋友们拿着冰冰的、甜甜的冰激凌,吃得很开心。我们还进行了文艺表演。我家曾有一次儿童节的集体照,可惜也在文革中被抄掉了。
梅汝璈、钟汉波及日本名流曾出席我们家宴
我父亲是四川成都人,母亲是湖南湘潭人,母亲擅长烹饪,四川菜和湖南菜都会做。加上当时家里经济状况较好,食物配给丰裕,父母常于周末在家举行宴会,招待本组和代表团的单身同事,有时也招待其他同事。
参与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梅汝璈先生,当时没带家属去日本,独自与国际法庭的法官们一起住在帝国酒店。他住的是一个套房,有办公间、会客厅和卧室。梅法官与国内联系需经由驻日代表团,因此常来代表团驻地。他平时住大酒店吃西餐,来代表团办事后和周末都常到我家来吃家乡菜。印象中梅法官很健谈,每次他到家来做客,满屋谈笑风生。
印象很深的客人还有钟汉波,他是海军少校,衣着与众不同,是白色的海军服。我们小朋友都喜欢和他玩,在雪白的制服上留下很多黑手印。
还有日本名流到我家来做客,有时还参加宴会。日本客人常常称道母亲的厨艺好。父母知道当时日本家庭大多生活艰苦,很多名流家也不例外,就不时特意分留一些美食让日本客人私下带回家去,给他们的家眷分享。可惜我那时年幼,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要是父亲健在,定能回忆起一些。
关于东京大审判
当时,东京大审判正在进行过程中,审判庭设在日本士官学校。中国方面为壮大中国听众人气,动员代表团团员轮流参与旁听。中国代表团成员有资格坐在贵宾席旁听。由于日本侵华罪恶滔天,相关法律文书众多,加上每读一部份就要用多种语言翻译一遍,整个过程非常冗长枯燥,但家父和团员们都尽量抽时间前往支持。
1948年3月,东京国际法院在进入判决程序前突然宣布休庭,中国驻日代表都很惊讶和气愤。梅汝璈来我家,家父向他询问为什么会休庭。梅汝璈解释了其中缘由:日方辩护律师宣称,日本战犯只承担战败的责任,不承担战争的责任,并通过大小媒体大肆宣扬,此说竟然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法官的支持,导致法官们的僵持。直到3月后,各国才达成协议,确定以政治需要决定法律的原则,完成对战犯的判决和执行。
在中国方面指挥下,父亲和同事、海军少校钟汉波等人协力完成了几件大事:将两个参加“百人斩”的狂魔引渡回中国审判;将甲午海战中“镇远”“靖远”两舰的舰锚、舰链及炮弹等从上野公园索还。这批被虏物后转到青岛海军军官学校陈列。1959年,“镇远”舰铁锚被送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2006年9月1日《东京审判》在成都首映时,梅汝璈先生之子梅小璈还专程拜会家父。此事成为新闻报道焦点,两人因此留下不少合影。
随父回国返乡 日本女佣恋恋不舍
1948年10月,父亲奉命回国。我们当时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返航的,这艘海轮是上海-东京-旧金山航班,很多海外中国名人都曾乘坐这艘2万吨巨轮,例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当年就是乘坐此轮归国的。
离开日本前,我们家的两名日本女佣都恋恋不舍,洒泪告别。由于当时日本社会总体上非常贫困,而我们家享受盟军外交官待遇,经济状况比较好,父母又不歧视她们,待她们很友善,她们在我家服务收入比很多相似工作的亲友都高,因此很珍惜她们的工作。她们俩年龄当时都20多岁了,如果还健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父亲回国后,像当时很多民国军政官员一样,非常反感内战,便举家返回成都,并最终脱离民国政府。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及其子弟校,则于1952年撤销。家父日后写了不少在日见闻回忆文章。2007年4月家父去世,享年94岁。他生前很想念当年驻日代表团的同事,渴望台湾统一,渴望中日时代友好,不再重蹈国共内战、中日战争这两大历史浩劫。我也希望能有缘在有生之年见到一些昔日驻日代表团的小伙伴——不论是随父母回大陆的,还是前往台湾或留在日本的。
本站编辑:杜瑞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