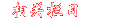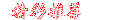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 祭父亲(04月16日)
- 祭扫先烈有感(04月15日)
甘惜分的探路人生
发布日期:2016-01-15 10:4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晋绥基金会
编者按
还记得2014年那个明媚的京城四月天,春风所至,处处桃李芳华。伴随着弟子们轻声浅唱的生日歌声,当时98周岁的甘惜分先生笑吟吟起身,没等摄影师调试好镜头,就干脆利落地吹灭了跳动的烛焰,举手投足间尽显骨子里的爽快与率直。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简单率真的老人,却在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走出了一条并不简单的人生路途——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投身戎马,到冒着纷乱炮火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再到后来步入杏坛传道授业解惑,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探索。数十载的光阴流转,甘惜分的每个转身都是果敢的。
谁也未曾想到,噩耗来得那么突然。甘惜分,这位著名新闻理论家、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于2016年1月8日22点5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本已写好的文章还未刊出,斯人已逝,深感痛心与愧疚。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谨以此文告慰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35年,甘惜分在重庆。
“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对新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的勤勉付出,让甘惜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者”的身份被人铭记;“宁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与执着坚守,则愈发彰显着一代大家的清亮品德与人格魅力。
如同美酒陈酿,甘惜分的丰富阅历与精深学养,随着岁月的积淀而历久弥香。
头顶耀眼的光环,甘惜分却总是强调,不要把他夸得太过了,不要给他戴各种高帽子,自己真正中意的是被称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先驱者”和“引路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甘惜分都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追寻。
探路革命
1916年,甘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就不得已辍学,成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员。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为了与先进思想保持同步,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历经苦难的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还在山沟里时,我就已经从上海的进步书报里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上海都是些进步知识分子,比如说李公朴等人。”
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的引导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共产党人熊寿祺,彼时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初中毕业后便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过书信拓宽了好友的革命视野。
进步书报与良师益友,潜移默化间促成了甘惜分的思想激变,血气方刚的他开始以实际行动“闹革命”。一方面,他团结县城进步青年成立秘密读书会,并在抗战爆发之后将其改组为抗日移动宣传队,以歌曲、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而另一方面,他也在积极支持地方的进步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形势风云突变,华北国土之内竟容不下一张书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成都,正碰上‘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
然而,那个年代,邻水县还远远算不上是进步青年的理想国。“那个时候连读马克思主义都是很困难的,而且可以说是‘犯规’的。别人会想,‘哟!这个人在看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就会向上级报告。所以学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偷偷读。”谈起读“禁书”面临的重重风险,甘惜分却格外淡然,甚至连讲述的语调都充满了轻松调侃。
“我到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思想提升,在熊复的邀请下,甘惜分欣然赴约,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旅程。
1938年,甘惜分抵达延安,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很快转到中央马列学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专门攻读马列经典著作。
在甘惜分心中,延安是一个由真理和真知搭建起来的圣殿——
“我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是从延安开始。过去在四川的时候,上海出版的报刊有真有假,编译都是二手货,不一定可靠,但到了延安就不同了,我们认真读原著,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资本论》等,这些书都是经典著作。”
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延安也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真正起点。
1939年夏,党中央把多所学校移往敌后抗日根据地,甘惜分奉命跟抗大一起转移。当时适逢贺龙率领的一二〇师请求抗大派人提高干部的政治素养。就这样,年仅23岁的甘惜分,开始以思想为枪,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政治教员。
在一二〇师的高级干部研究班里,甘惜分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侃侃而谈,为教学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
1940年,由于战略需要,一二〇师紧急从河北赶回晋西北,甘惜分也随之在晋绥军区安家,此后历任中共晋西地方党校教员、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43年,甘惜分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不料遭日寇偷袭,不幸被俘。为了保护随身携带的机密材料,他紧急将文件包埋入地下,即便被日寇严刑拷打,也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党的机密得以保护。
四个月后,甘惜分抓住机会成功逃脱。死里逃生看似是命运的眷顾,然而要捱过这里边的每一关,无一不需要坚定信仰的支撑。
“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日后艰苦自学,才能有成。”
探路新闻
从延安到山西,甘惜分对革命的理解逐渐深入,而他的命运也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我先在《晋绥日报》,然后在新华社晋绥分社,慢慢学做记者。”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他一步步参与进一线的新闻实践。
一九四九年,甘惜分担任新华社西南分社采编部主任。
实际上,当记者,可以说是甘惜分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像邹韬奋那样,做一个能带给人巨大鼓舞的新闻记者。
在晋绥边区,这个梦想成功地照进现实。
1945年,为顺应国内外局势变化,甘惜分被调动到司令部,负责每天撰写军情报告送到新华社,在前线供稿,这就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发端。
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谈期间,甘惜分跟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初入新华社不久的他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
“在大同我看见日本鬼子,穿着军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一看就生气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还这么神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甘惜分回忆起这个令他义愤填膺的片段,“这件事让我觉得,新闻不一定要采访什么人物,有时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就会发现新闻。”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完成《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就这样,通过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建立起一套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当时,中共绥蒙区党委要创办一份《绥蒙日报》,甘惜分奉命调至此处,成为《绥蒙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又在农村,以一人之力,操办《今日新闻》小报,“每天就用一个小耳机听新华电台的新闻,把它们誊抄下来,贴在村口路边的墙上”。
1947年,甘惜分进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感动几代人的刘胡兰烈士事迹,就是在这个阶段经甘惜分之手亲自修改、编发的。
短短两年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对于那个年代的前线新闻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独到的感触——
“老实说,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无论是《晋绥日报》还是新华社晋绥分社,有些同志由于没读过马列著作,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对工人社会的了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想,幸好我读过《资本论》,这些书不容易读的咧!因为当时我们的环境是农村环境,不是资产阶级环境,我们接触的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些关系很不利。”
1949年,甘惜分应中央要求前往重庆,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我自己是采编主任,但我还是经常到基层去采访,当时我们刚把国民党赶走,在采访中了解到国民党对人民的残忍呐,无情呐……我在重庆这段了解了很多情况,也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不少消息。”
任职期间,甘惜分不仅报道了蒋介石逃离重庆时下令屠杀政治犯的惨案,还报道了成渝铁路从动工到通车的全过程,更见证了新中国工业由弱变强的崛起之路。
回首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这段历史,甘惜分无限感慨——
“全部解放后,我们进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地方工厂有很多,不过这时的工厂都是国营企业,资产阶级的大工业都改成国营的了,完全的私营企业都很少了,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了解了更多工人阶级的劳动。”“101钢铁厂是重庆最大的钢铁厂,我在这里面采访了很多次,了解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感觉到钢铁工业是国家最基础的工业,一个国家连大工业都没有是强大不起来的。”
“没有摸爬滚打不行哦,哪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从一名政治教员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甘惜分在新闻之路上的成长与探索,的确离不开“摸爬滚打”。而这数十年的实践和摸索,也为他日后的理论思想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探路理论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为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奉献才华,主要讲授新闻理论。“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甘惜分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对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实的写照。
1982年,甘惜分(左)与方汉奇应邀到东北教学。
“我1954年到北大(教授新闻理论),当时新闻系什么都没有……我就慢慢地,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摸索。”阅读马列经典著作长大、革命前线采写经验丰富的甘惜分,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汲取精华,他甚至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追求、发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新闻阶级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对人民负责”“对真实负责”……凭着不服输的劲头,甘惜分按往日的经验,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
然而,在那个运动频繁、斗争混乱、意识复杂的年代,新闻学学科草创,种种问题尚未定论,许多概念、许多思想、许多观点不免发生激战,尤其当政治大潮裹挟了学术研究汹汹而来时,甘惜分仍始终捍卫着心中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1957年,在第二次首都新闻座谈会上,甘惜分批评了当时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观点,此后更是多次批判这种观点偏“右”。他认为,王中的意思是新闻是商品,这个他不否认,但他反对王中把商品当成报纸的本质属性,因为新闻更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是一种反映人民情绪、对人民进行教育的工具,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商品。
“这个老兄年纪比我大一点,他没有到过延安,一直在上海,对上海小资产阶级懂得多一点,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了解很少,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我是在延安长大,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王中并没有抓到资本主义的实质。”回顾往昔的论争,甘惜分细致地解释了自己批判王中教授的原因,声音中充满了平静与坚定。
说者无意,然而在激烈的政治浪潮中,原本正常的学术论争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对王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成为甘惜分心中难以磨灭的心结。“讲老实话,我觉得我当时批判他并没有错,只是态度太尖锐了,这是我应当做的检讨。”
然而谁能想到,时过境迁,仅仅过了两三年,当年的批判者却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一方面让甘惜分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冲动和莽撞,另一方面,直率和敢言的性格,也推动着他奋起反击捍卫真理。
1960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在批判附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言行,在紧张的斗争局势下,上上下下人人自危。5月,部分激进分子从系里教师的讲义中硬扯出800多条可疑字句加以批判。
然而,在甘惜分看来,这些人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甚至无知到把对的马克思主义语句当成了修正主义。出于对这种“左派幼稚病”的反感,他向那些批判者发起了义正词严的批评,这也招致了对方更为猛烈的回击。
极“左”者给甘惜分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右派”的帽子。在对极“左”者作出反击的过程中,甘惜分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武器,充分展现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学者风范。
当极“左”者揪住其“报纸是读者观察生活的学校”的观点,污蔑甘惜分鼓吹旁观时,他不卑不亢,马上拿出《列宁全集》回击,指出列宁论辩证法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
时隔多年,谈起这段经历,甘惜分依旧傲骨铮铮——
“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没读过什么书。我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多年,还给部级高级干部讲过课,又在新华社待了十年,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经据典和他们争辩,结果,辩来辩去,他们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们。”
终于,直到1961年,在中宣部的调查下,甘惜分的观点被肯定,极“左”者的嚣张气焰也偃旗息鼓。在全国都在“反右倾”的局势下,他却勇敢跳出来“反左”,并且获得了胜利,此间的胆量与智慧,实非常人所能及。
采访中,甘惜分多次掷地有声地强调:“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种种争论给自己带来的纷扰,甘惜分举重若轻,“我就是这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自投罗网,闯进这个‘无学之学’的圈子里面来研究新闻学的”,与他人的争论,也只是为了探讨新闻这门科学的规律。
正像甘惜分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中诙谐的自嘲那般,几十年来种种遭遇,无非是“被卷进漩涡,呛了几口水,眼见几家欢乐几家愁,自己也成了一只落汤鸡,又打而不倒,死而复生,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自己的追求”。
甘惜分说,他甘愿做真理之神的马前卒,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恰恰就是这位新闻理论大家最坚定的精神皈依。
探路教育
挺过了“反右倾”浪潮,1968年到1978年,甘惜分又遭遇了十年浩劫,对于此间种种心酸与委屈,他鲜少提及,他甚至认为这些苦痛无足挂齿,因为“这些往事,好多人都能背诵一大篇”。然而,在政治运动中浪费的精力和虚掷的光阴,却成为老人心中长久的遗憾。

2015年8月31日,甘惜分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而实际上,不论是在下放劳动中,还是在派系论争中,甘惜分都没有停止过对新闻学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只想大事,不想小事”的豁达性格,不仅让他在艰苦的环境里释怀了个人苦难,还让他的思想在更广阔的天空里翱翔。
甘惜分在一篇自述中感叹——
“我有约100个笔记本,记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以便随时运用。我这人很笨,记性也不好,只有笨鸟先飞,下些笨功夫。从1954年到1980年,这26年中大多在政治运动中瞎折腾。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到了老年才进入角色,悔之晚矣!但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必须站出来!”
1980年,64岁的甘惜分果然“站出来”做了一件惊天之举——他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挥汗如雨,夜以继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新闻理论基础》的初稿!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1986年,甘惜分又创作了《新闻学原理纲要》,不但进一步证明“新闻有学”,而且借此重构了自己数十年来对新闻工作规律的理论认识。
“这两本书都是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新闻怎么看待的问题。”甘惜分向记者讲述这两本书的意义——
“1954年我到北大新闻专业讲课,在我之前没有教材,我就是中国新闻理论教材的创造者,所以他们叫我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者。奠基者、先驱者、先行者,这都可以说,我是在前面带路,发表了一些意见和观点,但是我没有说完成了,我是打了个基础,不要夸的太过分了。”
此外,1986年,甘惜分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1988年,其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1996年,80岁高龄的他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与心路历程铺陈于纸上,完成《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
“从1954年到大学当教授都几十年了,我觉得我的理论从基本原理来讲是对的,当然是不是很周到,我也在不断修改,使我的理论更加周到,更加完美。”
于是我们看到,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为了完成对前半生理论成果的修订,甘惜分的思维方式日渐向更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新闻理论思想越来越向广大人民群众靠拢,甚至无惧于“在刀尖上跳舞”,论说他人不敢言之言。“打破报纸的舆论禁区”“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新时代的媒介学人和工作者提供了切中时弊的指导。
而其在学术道路上的披荆斩棘,则愈发印证了甘惜分反复提及的那个成语——认识真理是逐步的发展过程,在求知的进程中,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而来。
从教几十年,甘惜分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老祖师爷”,其亲自指导的博士生虽然不多,但每一位都是当今新闻传播学界的精英翘楚:全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广电部门的王锋、王甫……怪不得有诗赞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喻国明回忆:“甘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不敢和老师争论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超过老师的学生,也不是好学生。”这种另类的激励法,或许更表达了一位学术“大家”的气度和胸怀。
一个偶然机会,笔者了解到,甘惜分的这群优秀门生,正在筹备一项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基金的项目,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一学科在中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然而,当被问起当下的进展时,甘惜分却少有地面露难色:“这可难说,我是反对他们的,因为要把我搞得像个创始人,我可不干这种事,自卖自夸,多不好。咱们呐,还是做些具体工作,不要夸大自己。”短短的话语里,还是那份率真和坦诚,让人不禁赞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甘惜分说,他“愿意做一个终生求索的学生,不求名,不为利,只图为人民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的通融与倔强、无畏与谨慎、愚拙与智慧,都让这恍如云烟般消逝的岁月变得充盈饱满。
采访的最后,笔者问起甘惜分对“当今新闻教育中欠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观点的看法。他认真地给出了回答:“不能说是教育中有欠缺,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达到。很多搞新闻的人自己懂得马克思主义吗?不懂。”谨以此意味深长的话,留给广大新闻人反思。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