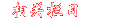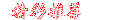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悼念晋绥老前辈毛大风叔叔(07月20日)
-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襟怀(07月08日)
- 一场别开生面的视频签约(04月30日)
- 林炎志:继续做好铺路石(04月27日)
- 黄河古渡黑峪口 “两弹一星”晋绥情(04月08日)
- 六百英灵—远方山中的牵挂(04月02日)
- 怀念老红军张文阿姨(03月29日)
- 想起贺老总在晋绥(03月21日)
- 虎年初春晋绥情(02月20日)
- 怀念“四八”烈士后代—秦新华大姐(02月16日)
老一辈革命家张稼夫长女张尔可回忆
在兴县度过的那段少年时光
北京/张尔可
1938年,母亲将我送到延安,我是在延安的保育院、保育小学和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生活、学习、长大的
1945年初夏,我告别生活了八年的延安,来到晋绥边区的首府山西省兴县,与我久别的父母团聚在北坡村。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曾断断续续地失学近两年,这对我学习文化知识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也使得我有机会接触了社会实践,学习到了一些子啊课堂上难以得到的知识,对后来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的晋绥边区,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已成为有三百多万人口的稳固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坚固的屏障,也成为各解放军通往延安必经的交通要塞。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贺龙师长领导的120师,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指示,抗日战争节节胜利,民主政权得以稳固,军民过上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刚刚召开过的边区群英大会表彰了抗日劳动模范,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边区文艺大会的召开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现象。
我时年十岁,由于失学在家,每天都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于是走东家串西家,与北坡村的百姓朝夕相处,对各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为此,人们送我一个外号,叫“北坡村长”。时光过去六十多年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应《乡音杂志》赵主编的盛情约稿,现将几件往事回忆如下。
军民鱼水情意深
印象中的北坡村是一个仅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这里却是驻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这个重要的机关。村里的群众把自家最好的窑洞让给了机关各部门办公和居住,而自己一家几口人挤在一起。那时候,除了重要的机要部门外,其他部门都不设岗哨。机关人员和群众之间相安为邻,彼此常来常往亲如一家人。机关为减轻群众的负担,自己动手纺纱种地,每当瓜果蔬菜收获的季节,经常送给群众共享。群众有了困难随时可以找机关的同志帮忙,谁家大人孩子有了病,妇女生孩子,都找机关医务所罗亨州医生诊治,一般都是随叫随到。
七月剧社和战斗剧社常来北坡演戏,村里的群众和机关的同志不分彼此,亲热地坐在一起观看。剧团演的节目大多紧密结合革命形势,我记得有《血泪仇》《闹对了》《张初元》《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白毛女》《刘胡兰》,传统剧有《打金枝》《走雪山》等,文艺生活异常丰富。
村里群众除了努力生产,积极缴公粮外,还主动帮助机关食堂碾米、磨面、做豆腐,那种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至今让我留恋不已,这种感情如今却少见了。我总是想,党和政府的干部如果真像过去那样,心里装着老百姓,我们定会战胜一切困难,实现复兴中华的伟大梦想。
我亲密的小伙伴们
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是村里几位年轻相仿的女孩子,有侯巧儿,驼则,在亲等。侯巧儿的父母都是勤劳老实的农民,印象最深的是老两口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地为机关大食堂磨面磨豆腐,很受大家的敬重。侯巧儿是他们唯一的掌上明珠,是个漂亮的女孩儿。她长我几岁,是个大姐姐。驼则的父母已过世,她和伯父、叔父母一起生活,是一个性格温柔,极为勤劳的女孩。在亲的父母也是老实的农民,他性格天真活泼,整天笑眯眯的。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亲如姐妹,从不闹别扭。夏天,大家相约一起去蔚汾河边放羊,还帮家里干点农活。我也牵着警卫连的一只绵羊,这只羊被我养熟了,我走到哪里它跟我到哪里,我很喜欢它。但过年被警卫连偷偷地杀了,我还以此哭了好几天。警卫连为了犒劳我,特意送来一大碗羊肉,我一口没吃。
北坡村的耕地大部分在山坡上,种着谷子、糜子、山药蛋、荞麦、莜麦、豌豆,这些早地庄稼全靠老天爷的恩赐,幸好那几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百姓吃饱肚子绰绰有余。蔚汾河的两岸是狭窄的水浇地,对老乡来讲,是珍贵的宝地,这里种着蔬菜和瓜果,小伙伴们经常将自家的水萝卜、黄瓜、甜瓜摘下给我吃。
到了冬天,家家炕上堆满了南瓜,坉里贮满了粮食,窖里堆着土豆,院子里腌着几缸酸菜和自制的醋,百姓的日子过的红红火火。我最喜欢春老乡家用西葫芦、豆角、山药蛋做的大烩菜,既当粮食又当菜。还有小米面窝窝和钱钱稀饭等。过年时的黏米面油炸糕至今让我垂涎欲滴。我不管到哪家,如果赶上吃饭,老乡们就留我一起吃,不吃饱肚子不让走,我成了个名副其实“吃百家饭”的孩子。我也经常把机关食堂的稀罕东西带出来分给小伙伴吃。我第一次吃平川送来的红薯时,觉着那么的香甜,味道好极了,于是用手绢包了几个捎给小伙伴尝鲜。
冬天地里没活干,我们常聚在一起捻毛线、纳鞋底、缝扣袢,我最初的针线活就是她们教的。有时,趁大人不在,我们就偷雪纺棉线,学织布,无意间中糟蹋了不少棉花。有时布匹也织坏了,为此,免不了受大人的责备。
贺龙伯伯和我的趣事
晋绥军区司令部就在距北坡二里地的蔡家崖村,他们经常来北坡开会。会议室大窑洞就在我家隔壁,我常见到贺司令和军区司令部的其他首长。贺伯伯很喜欢孩子,闲暇时总和我聊天,有一次,我闲得无聊,,就在我家隔壁的会议室给贺伯伯摇了电话(那时的电话就是用手摇)。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薛明阿姨,她问我是哪位,我学着我母亲的口气说:“我是王大姐啊!”她一听就知道是我在淘气,就哈哈大笑地说:“你是淘气的二狗吧?”我知道被大人识破了真相,立马将电话挂掉,后来这件事总被大人当作笑谈。
还有一次,北坡演节目,贺伯伯也来 看戏。节目开始前,他看我四处乱跑,就招手叫我过来有话要说。他问我:“你长大想干什么?”我在延安时就看到有人戴着飞行帽,心里很是羡慕,就想长大当个飞行员。于是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当飞行员。”贺伯伯听后非常高兴的说:“好啊!有志气,伯伯支持你,将来我一定要坐你开的飞机!”得到贺伯伯的夸奖,我心里十分得意,没想到他又补了一句:“不过,坐你的飞机时,伯伯一定要带上降落伞啊!”周围的大人听了一阵大笑,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贺伯伯又说:“你说个勇敢的女孩,好好学习,祝你愿望成功。”后来,我虽然没有当飞行员,但贺伯伯的鼓励一直鞭策着我,让我学习做事都不敢怠慢。
目睹晋绥土改的几件事情
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1947年初,晋绥边区开始土改运动。日本投降后,原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奉命开赴东北工作,我父亲张稼夫接任分局代理书记职务。土改初期,分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小册子,作为指导晋绥土改初期的政策依据。后来,李井泉同志担任了分局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康生、陈伯达也在临县和静乐县搞土改试点,他们执行了一套极左的错误路线,认为晋绥土改初期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进而发展到全国否定晋绥在抗日时期的工作,指责林枫、张稼夫为代表的原晋绥分局主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执行的也是右倾路线。随后,李井泉同志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斗争的矛头直指原晋绥分局领导。因林枫同志在东北工作,我父亲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会上有人说:“原晋绥地区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是地主阶级的政权(指三三制政权),是军阀头子的军队。”据说,贺龙同志听后大骂:“那老子不成了军阀头子了吗!”所以,后一句话以后再没人敢说了。这次会议决定收回《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小册子,对原有党政组织一脚踢开,县以下干部交群众斗争,对干部要“搬石头”“揭盖子”。会后,《晋绥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有事和群众商量》的讲话和《为纯洁党的组织而奋斗》的社论,提倡“群众要咋办就咋办”。从此,晋绥的土改运动在极“左”错误的引导下出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
那是我年仅十一二岁,对党内斗争情况一无所知,但以孩子的眼光,目睹了一些令人发指的时间。比如,北坡村斗争地主时,我看见小伙伴在亲的父母被吊在戏台上,用点燃的排香去烫他们,老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我心惊胆战。在亲的父亲对我说:“二狗啦(我的乳名),你救救我们吧!我们活不了啦。”可是,那些疯狂的人们,谁能听一个孩子的话呢?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想要我找我父亲来搭救他们。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我的父亲也正遭受批判,已被剥夺了对晋绥土改的领导权。
侯巧的一家也遭到了斗争,并被扫地出门,搬到石楞子的一个破窑里,有一天,听说石楞子村的一个光棍臭老大正在逼迫侯巧和他结婚,侯巧硬是不同意。我看见她披头散发地坐在墙角里哭个不停,回去告诉我妈,我妈听了很气愤。有一次,侯巧偷偷找到我母亲,说明她的处境,期望我母亲救救她。我母亲说:如果说,地主富农的财产是剥削来的,但子女并不是剥削来的,绝对不可以分配。她对侯巧说:“你放心。”之后,我母亲将侯巧的遭遇通过父亲反应给分局,有关方面责令石楞子村放了侯巧。
我还目睹了另外一件恐怖的事情,村里有个老汉把自家窑洞让给机关大食堂,自己挤在旁边的一孔窑洞里。土改时他被划为富农,因经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服毒自杀,被埋在村东的坡下。有一天我看见有群人把棺材挖出来并从中将他抬出来,说他家将浮财装进棺材里,但翻了半天也没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
我还目睹了轰动兴县的“斗牛大会”。那天蔡家崖的山坡上下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半山腰一个院门外站着一个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白胡子老人,他就是牛友兰。令人惨不忍睹的是他的鼻孔间被人用铁丝穿了一个绳套,还不时有人过来拽着绳套逼他缴出浮财,老人鼻孔流满鲜血,疼的全身颤抖,但他始终高昂着头一声不吭。随后叫来了老人的儿子,时任晋绥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同志,逼他和贫雇农一起批斗自己的父亲,此后发生的事情我真不忍心再细说了,斗争大会后不久,牛友兰老人就含冤而去了。
以上所见所闻对我幼小的心灵是一种极为残忍的摧残,它不仅令我震惊、悲愤和无奈,而且使我多许多问题产生了困惑和疑问。不由想到1945年的秋天,时任晋绥分局代理书记的父亲,曾在家里设宴招待过牛友兰先生,他们促膝相谈整整一个下午,气氛是那样的和谐。老先生走后,父亲告诉我,牛友兰先生是晋绥边区鼎鼎有名的开明士绅,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倾其家产捐献数万大洋资助抗战,开办了第一个边区银行和西北最大的纺织厂,是抗日有功之臣。他还和李鼎明先生率晋绥边区开明士绅访问团赴陕甘宁边区考察,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热情接待,因此,我对牛友兰先生很是敬佩。可是,时过境迁,昨日的座上客,却成为今日的阶下囚;过去亲如一家的老百姓,现在却遭遇到如此的摧残。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不久,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兴县,来到方山县大武镇贺龙中学,在那里又经理了“三查”运动。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一批文志革命的热血青年被清洗,他们被迫回到在阎管区的家乡,其中有人被捕,有人牺牲。更无法理解的是,从小在延安保育院和我一起长大的王锐玲(王达成同志的小妹妹)也被清洗,说她是地主的女儿。她根本找不到家,无奈又回到军校。
直到1948年,毛主席路过兴县,通过调查研究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召开了晋绥干部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严肃的批判和纠正了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毛主席说:“你们这里就那么一点马列主义的东西,还被你们烧掉了(指《怎样划分农村阶级》小册子)”他还对抗战时期晋绥的工作作出评价,充分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我是在贺龙中学学习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解开了心中的许多疑团,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坚定了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
回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对晋绥的土改革命运动应当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土改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晋绥土改中出现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低估,如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的纠正,革命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破坏性是很大的,事实证明左倾路线害死人。这惨痛的经历教训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大反攻,我参加贺龙中学宣传队,走遍晋中十四个县城,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在新区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慰问前方作战的子弟兵,配合西北军政大招收了二千多名知识青年参军,在临汾经过短期学习训练后投入了全国的解放战场。
永远思念这片热土
为了建设新中国,根据组织的决定,我于1949年夏天进入东北实验中学读书,1956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长达十七年。“文革”后又调到国家科委从事农业研究管理和科技奖励工作,至1995年离休。
离开兴县已半个多世纪了,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已成为古稀老人。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忘不了兴县和北坡村的父老乡亲,忘不了亲如姐妹的小伙伴们。上世纪80年代末,我那八十对岁的老父亲专程回到兴县和北坡村,看望八年抗战同甘共苦的乡亲们。他回来后对我说,北坡的乡亲们非常想念你,你一定要回去看望他们。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专程回到兴县,探望了北坡村的父老乡亲。老人们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你就是那二狗啦?可想死我们了,你小时候可害人(指淘气)哩!”他们带着我看了我家当年住过的窑洞,还指给我;这是林枫家,那是龚子荣、龚逢春、王达成、宋应、许荒田……的家,还领我看过马烽、西戎写作《吕梁英雄传》的大众日报社旧址,还有机关大食堂。这些故居虽已破旧不堪,我仍然觉得还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驼则的叔父请我进他家拉话,回忆当年的许多往事,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他告诉我,驼则现名牛进香,在贵州省工作。侯巧也参加了工作,现住兴县城里。在亲远嫁他乡。这次没见到小伙伴,心里很遗憾,但得知他们现在过的都好,很是高兴,真心祝愿他们晚年幸福快乐!
1990年,我父亲张稼夫与世长辞。遵照他生前的遗愿,我们将他的骨灰送回兴县,撒入黑峪口的黄河之中。这是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他深深地热爱这里的人民,眷恋着这块热土。兴县党、政、人大、政协在黑峪口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许多乡亲自动前来为他送行。
我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兄弟姐妹四家再次来到兴县黑峪口,我这才发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兴县人民为父亲立了一座丰碑,碑石上镌刻着时任县长郝柏耀代表全县人民书写的一首情深意长的碑文:
身卧故地水棺眠
古渡船笛报更点
黄河滔滔伴君舞
戎马铁笔代代传
这碑文充分地表达了兴县人民对这位已故老战士的深切怀念之前,我们为之感动的热泪盈眶。作为后代,我们真心感激兴县的领导和人民的深情厚意,我们要像父辈们一样永远热爱这里的人民,永远眷恋这块土地,将老一辈未尽的崇高事业代代传承下去。
张尔可,国家科技部离休干部,革命家张稼夫、王亦侠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