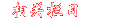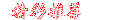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悼念晋绥老前辈毛大风叔叔(07月20日)
-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襟怀(07月08日)
- 一场别开生面的视频签约(04月30日)
- 林炎志:继续做好铺路石(04月27日)
- 黄河古渡黑峪口 “两弹一星”晋绥情(04月08日)
- 六百英灵—远方山中的牵挂(04月02日)
- 怀念老红军张文阿姨(03月29日)
- 想起贺老总在晋绥(03月21日)
- 虎年初春晋绥情(02月20日)
- 怀念“四八”烈士后代—秦新华大姐(02月16日)
我的岳父林枫
发布日期:2015-05-27 13:3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罗箭
♦作者罗箭简历:
罗箭,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1938年出生在延安。1958年从 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后,是哈军工第一届原子能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新疆某核试验基地。在“文革”期间,其父罗瑞卿受到迫害,罗箭也未能幸免。1970年复原到南充当工人,1976年,落实政策后重返新疆。1978年,调国防科工委机关工作,1996年,从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岗位上退休。少将军衔。
林枫是我的岳父
罗箭,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1938年出生在延安。1958年从 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63年毕业后,是哈军工第一届原子能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新疆某核试验基地。在“文革”期间,其父罗瑞卿受到迫害,罗箭也未能幸免。1970年复原到南充当工人,1976年,落实政策后重返新疆。1978年,调国防科工委机关工作,1996年,从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副政委岗位上退休。少将军衔。
林枫是我的岳父
我和耿耿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黑暗的1970年结婚的。我们过去并不熟识,甚至没见过面。结婚之前我对耿耿的父亲林枫,也了解极少,只知道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校长,“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算作“刘少奇黑线”上的“大干将”。我的父亲罗瑞卿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当然也是一个大“黑帮”了。在那个年代背上“黑帮子女”名分的人,属于当时的“地、富、反、坏、右、黑”六类分子中的最底层,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这样,我们两个被别人嫌弃的人,走到了一起。这是历史的误会,但却是我们个人的喜事。若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真没有我们这对夫妻。

左起:罗箭、林枫、郭明秋、林耿耿,摄于阜外医院,1973年夏。
被关六年后,终于有了音信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家政治形势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这类孩子开始纷纷写信给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与被关押的父母见面,竟都被准许了。见了父母面的人们奔走相告,各种消息不断传来。于是,1972年7月,耿耿的姊妹们也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寻找六年里杳无音信、生死不明的父母。当时只是想通过写信,试探一下父母是否还活在人间,没想到很快被批准与父亲见面。
1972年8月5日上午,几个闺女、儿子从贵州、山西、河北、四川、黑龙江的山旮旯和专政机关的“学习班”里聚集到北京秦城监狱,见到了形容枯槁、濒临死亡的父亲。这次见面,全是闺女们“发言”,关押了六年的父亲听“傻”了,几乎没话。但他说出来的几句话,却被在场的每个孩子牢牢记住了。岳父说:“前些日子,《人民日报》上登了解放战争时,我军战士解放锦州,路过老乡的苹果园,没有摘一个苹果的事。当年,毛主席曾就此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活下来的。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林树乐’,树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毛泽东批示放人
从秦城监狱回来,由老大梅梅执笔,连夜再给毛主席写信,力陈根据岳父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请求放他出来治病,并描述了岳父讲到毛主席“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信是通过王震同志当时的秘书伍绍祖转上去的。
8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见《毛泽东传》下册,1619页)8月17日上午,林枫专案组一负责人,匆匆忙忙来到我们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赶出原住所六部口内翠花湾3号后的住宅——和平里1区5号楼10单元303室,让孩子们不要忙着返回各自劳动的工厂、农村,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你们的信,毛主席意放你父亲出来治病;明天就接你父亲到心血管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住院治病;毛主席批评我们对你父亲搞了‘逼供信’,我们要向毛主席检讨,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做了检讨,我们将来还要向毛主席做检讨。我们也要向你父亲做检讨……”
8月18日上午,我们来到阜外医院六病房西头第三间病室,岳父早已在那里了。病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岳父的,另一张是看守人员的。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五年断断续续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接触,直至1977年9月29日下午7时50分,他在这间整整住了五年的病室里含冤去世。

1945年在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照片。
第一次见到岳父
1972年8月,我第一次到阜外医院看望岳父林枫。在这之前,我还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不免有些紧张不安。他第一句话就说:“中国的老话:子婿、子婿,女婿和儿子一样,都是儿子。”一下子解除了我的窘迫。以后去得多了,慢慢了解了岳父的脾气秉性。岳父是个性格内向、言语极少的人。他性格沉稳,见地深远,话语不多,说出来的,却总是一针见血。不论是谁,我们,还是老同志们去见他,都可以长时间坐着不出声,只有相互的眼睛和心灵交流,却也心安理得,一点儿也不尴尬。甚至他唯一的儿子林炎志去看他,也可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么干坐着,爷俩谁也不吭声。最后是儿子说:“爸,我走啦。”老爷子回答:“嗯。”这就是岳父的典型一面。
专案组的人说,你岳父是党内著名的话少的领导人,平均五分钟一句话。他们审问了岳父多年,定是深有体会。但我能体会到,他是很想和我们说话的,特别想听我们谈谈社会上的见闻。每次去医院陪护,基本上都是我们滔滔不绝地说。大道、小道、坊间传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股脑儿倒给他。大部分时间他只是听,不加评论,但偶尔冒出的一句话,却都是画龙点睛之笔。说到“四人帮”借“批孔”,矛头对准周总理、邓小平,批“大儒”和他背后“更大的儒”。岳父冷笑了,说,“怎么了?沉不住气了。看来他们的气数也快尽了。”打倒“四人帮”时,住隔壁病室的任白戈伯伯的儿子任嘉因,冲进岳父病房,大喊:“林叔叔,你胜利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岳父也只是笑笑。
我看出来了,他又想听我们说,又怕我们言多必有失,有时候也不免流露出不满我们做派的情绪。就拿1972年8月18日上午,在阜外医院见我们的第一面说吧,那时他刚从秦城监狱“半解放”出来几小时。我们见面后,梅梅马上把前一天专案组负责人说的、毛主席对我们信的批示和专案组向毛主席检讨的话,告诉岳父。岳父听后,说:“这个话以后不要再讲了。这些人都是群众,并不了解情况,是有人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全怪他们。这个人(指专案组的人)对我比起专案组里其他人还算是好的,他没有对我动过手,态度也不那么凶恶。”岳父一再重复了这几句话……
岳父总是教育我们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他常说:做人,无论什么时候说话、办事都要稳重、稳妥、稳当;能一句话说完的,不说两句,别老说那些没用的话;说出来的话就要负责任,不能说无凭无据的话,更不能说假话;要说就当面说,背后不说;不知道的就别说,不懂装懂……
岳父的沉默寡言是怎么来的?
岳父去世后,岳母郭明秋给我讲了许多岳父过去的事,我才体会到,岳父沉默寡言,有性格使然的原因,也是长期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后来又久处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心,使他谨慎有加,再加上历史的厄运频频光顾他,使得他更加沉默寡言了。
1975年底,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的老领导张爱萍同志复出,为了落实政策,把我和耿耿从我的老家四川省南充市第二缫丝厂调回。我仍然回“文革”前的工作单位,新疆的核试验基地。耿耿到国防科工委第十研究院情报室工作。1976年年初,形势陡然紧张起来,张爱萍同志几次催促我尽快离开北京回新疆。当时两边的父亲都是疾病缠身。身为子女,轮流在医院照顾他们,这是我们最后尽一点孝心的机会了。但为政治形势所迫,只好依依不舍地走了。1977年9月底噩耗传来,岳父病逝。我匆匆从新疆赶回来,也未见到岳父大人最后一面,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岳母郭明秋
1978年我调回了北京,和岳母同住一院。岳母郭明秋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夕,受北平地下党组织——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党团书记彭涛的指派,假扮成北平一家很有影响的大报记者,到当时我母亲领头搞抗日爱国活动的北平女子职业学校里(现地安门西大街厂桥东官房附近),与我母亲接头并了解情况,回来后向彭涛等党组织领导人汇报。这样,我岳母就在革命工作中认识了我母亲。她们是白区秘密工作战线上的优秀战士,也是好姊妹。
1937年11月,母亲怀着我,迎接了第一次到延安的岳母,和父亲罗瑞卿以及父亲的同乡、同学、同庚任白戈同志一起聚会了一次。当时我母亲正在党校学习。她在北平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延安找不到知情者证明,见到岳母,大喜过望。“文革”中岳母虽深陷囹圄,但又一次为我母亲的党籍问题作证,所以我对岳母的感情、对岳父一家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真觉得老天爷有意安排我做了林枫、郭明秋的女婿,真是缘分啊!就像岳父第一次见我时说的那样:子婿、子婿,女婿和儿子一样,都是儿子。
1991年,耿耿调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一走就是整整八年。我身上就多了一副照顾岳母的担子。无论是我推着轮椅上的岳母在南沙沟的院子里散步,还是在她的病榻前,谈论最多的当然是岳父林枫。我成了岳母最大的倾诉对象,有很长时间,岳母讲,我记录,成了每天必须进行的功课,这使我对岳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岳父的一生
2006年同是我父亲罗瑞卿、岳父林枫,两位父亲的百年诞辰。为了岳父百年纪念,耿耿放弃了派她去国外使馆长驻的工作安排,下决心提前三年,于2003年底从外交部退休,自觉、自愿、自费、专心一志,投入到准备工作中去。我支持她这样做,也帮助她收集资料,采访了许多与林枫、郭明秋有关的人,使我在走近林枫的道路上,对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岳父一生的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岳父在血雨腥风中投身中国共产党,至“七七”事变,主要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白区地下工作达十年之久。作为刘少奇的政治助手,除了和敌人斗争,还要和党内错误路线,特别是“左”倾冒险主义做斗争。长期的秘密工作使他沉默寡言,谨言慎行。
第二阶段是在山西晋绥根据地抗战八年。这是他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他身心最愉快的八年。他从白区地下工作转变为公开工作,由地方工作转变为地方加军事工作,使他有了发挥自身领导才能的用武之地。他团结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和贺龙、关向应等同志一起创建了晋绥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1937年7月8日,山西孝义县碾头村,八路军115师师部,纪念抗战一周年合影。前排左起:张友清、郭明秋、张月琴,二排左起:林枫、杨尚昆、罗荣桓。
第三阶段是日本投降后,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东北地区的九年。他作为东北地区党组织和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虽然做了大量的政权建设、后勤支援工作,但他的功绩往往被当时军队的骄人战绩淹没,在大量的党史资料以及文艺作品中没有他的身影。而且他坚持党性原则,绝不同流合污的人格,也为林彪、高岗等人所不容,使他长期处于被打压的状态。为了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党的团结和工作大局,他总是委屈自己,从不争闹,对高岗等人的无理一笑置之。对丧失党性的事默默抵制,不告状、不推诿,多一句话也没有。而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说话了。
岳父批评高岗的个人主义
195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沈阳,用整整两天的时间(26日、27日),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3月31日,就在这次东北局高干会上,岳父发言说:“高岗给我们最坏的影响是个人太多了,党性太少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党性,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了,那末他的职位越高,出的乱子也就越大。”岳父痛心地总结道:“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提高党员的党性的工作,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党性,提高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的修养,决不要把一个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里去,我们大家都要警惕!”
在这次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一向少语的他,却铿锵有力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从高岗事件中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加强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个人主义和骄傲情绪对党的严重危害性。”岳父切中高岗问题的要害,首先直点“党性”,而没有一句泄私愤的话。在岳父去世几十年后,还有知情的与会者特别指出:“林枫同志当时的这些话是画龙点睛之笔,是什么时候都不过时的党内教训!讲得太重要、太好了,字字千斤啊!”
第四阶段是1954年至“文革”,在北京、在中央工作了13年。他主要协助周恩来总理抓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工作。他同样是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从不张扬,以至于现今某些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工作史的人,都不知道有林枫这个人,更不知道当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校六十条”)是林枫领导下出台的。
1963年初,受党中央领导人的指派,岳父接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领导工作。他又一次陷入了斗争的漩涡。他虽然以宽广的胸怀尽量团结更多的人,但还是有少数人对他说三道四。“文化大革命”开始,康生很快就把他抛出来,使他又一次为党内斗争作出巨大牺牲。
岳父这一代人
岳父他们这一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常常思索这个问题。我们后代要想准确、精练地说出来是十分困难的。岳父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性。现在我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上了解了他。我想,自己已能,至少是自以为能粗浅地理解他了。他们这一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是极其虔诚的理想主义者,又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投身到共产党内是因为他们坚信马列主义可以救中国。
岳父这一代人,特别是领导人,大多出身殷实之家。他们本来不缺吃穿,在那个社会中混个一官半职也非难事。但他们选择了革命,因为革命可以解救国家和民众。他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甚至生命,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可以抛弃一切。他们是为信仰加入共产党,不像现在一些人是为了利益加入共产党。我的岳父、我的父亲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这一代人都是这样的人。这是他们的共性。
这群人又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有的豪放、有的拘谨、有的善于待人处事、有的棱角分明。岳父禀正直之性,怀刚毅之姿,嫉恶如仇,见善若渴,讲究对党组织、对老百姓、对事业忠心耿耿、本分老实的言行举止,既重大节,又重小节。他不是完人,也有缺点,但他极其看重自己的名节和修养。他自己如此,教育、要求子女也是如此。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低调的,不张扬,秉承从善如流,宁愿委屈自己,从不伤害同志。了解他的人极尊重他,反对他的人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关山复叔叔曾评说:“古人云‘君子可欺之以方’。林枫是君子。林彪、高岗就是利用了林枫同志惟党性原则是崇、品德高洁这一点。这帮人卑鄙无耻就在于此!”
含冤而逝
1977年岳父身体每况愈下,自知不久于人世,他最痛苦的是,“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秉承林彪、康生与“四人帮”之旨意诬陷他“伪造历史、混入党内”,不承认他是1927年春在天津入党。岳父为了能获得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分,违心地同意自己的党龄从1931年算起。因为这个时间在“文革”当时有人敢于证明,即赖若愚、顾卓新同志。他对岳母说:“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我死了,身上就不会给我盖党旗;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的话,我死了,孩子们算什么?你算什么?”耿耿姊妹们陪护在病房时,曾半夜里被岳父的喃喃自语所惊醒,只听他说:“唉,这个党是我自己主动找上门去的呀!”可以看出来这件事令他痛苦不堪,但为了自己的名节,他只能转而求其次了。1977年9月29日,岳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尽管这样,当为他举行追悼会时,当时还把持中央某些部门权力的人,仍坚持岳父身上只能盖白布单,而不准盖党旗。10月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大会,由吴德主持、胡耀邦致悼词。在现场,岳母从一开始就和这些人当众公开顶撞起来。这些人就硬是不准给岳父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不准在悼词中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剑拔弩张、针锋相对、一点火就着的尖锐场面,有上百人目睹。有着整整五十年党龄的岳父,临走也没有享受到一名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最后的要求。
身后党籍方得恢复原貌
岳父走后,岳母继续战斗,她依然不减50年前“一二·九”运动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的锐气,带上儿女找到陈云同志、彭真同志,一而再地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反映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和我岳母的谈话,有这么一些内容,应该记录在这里。
陈云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亦艰难困苦异常,而岳父仍强有力地支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从实物乃至硬通货。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所以对岳父的业绩非常了解。陈云着重讲到岳父入党时间问题。因为岳父是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陈云说:“入党时间应以七大代表登记表为准;那时写的是哪一年,就是哪一年。”“当时的审查(指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很严、相当严格。”“那个时候没有压力,人(指证明人)也 都在,可以证明;不是那么好蒙混过关的。”
在彭真、陈云同志的直接证明和关怀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在林彪、康生与“四人帮”的阴魂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岳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见证者开始承认自己曾是中共党员并说出史实真相(此人的中共党员身份也有中共领导人的直接证明)。在粉碎“四人帮”八年之后,岳父离开我们七年之后的198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终于发出《关于林枫同志入党时间问题的通知》,指出林枫同志的入党时间是1927年春天,恢复了历史原貌。可惜,岳父已无法亲眼见到这一切了。
岳父留给我们的遗产
回忆是为了纪念,纪念是为了继承。我和耿耿在后来自己的政治生涯中,都担负过不同单位的党委书记职务。岳父的革命历程和遭遇,使我们在本职工作中对实事求是原则有了自己的真知,并把实事求是融进思想和行动;岳父的革命历程和遭遇也使我们懂得了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是要付出名誉、职位乃至身家性命的。特别深悟到凡从事政治思想、组织人事工作的人,能否实事求是,这是个要害问题、是对自己政治品德的考验。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乃至此人全家的政治生命攥在你手里,你该怎么办?你会怎么想?岳父岳母生前身后、有形无形的言行,都在我和耿耿心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我们的家风,也是我们为人品行的标志。要知道,在和平时期坚持实事求是亦非易事。“惨痛代价”已不能准确描写出岳父岳母一生的付出和我们的实践。
在岳父出狱后,耿耿曾力劝岳父口述自己历史,由她记录下来,免得将来再有政治运动,下一代又有说不清的地方。岳父不肯讲,任由耿耿劝说,怎么也不肯讲。岳父说他的历史“中央清楚、中央了解”。还说,解放前一些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组织上要求他们终生不能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甚至顶着叛徒、特务的名分一辈子,死后都不能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一生,却不能得到党组织的承认,对岳父这些人来说,是最大的心痛!
岳父离开我们已整整36年了,我反而觉得离他越来越近了。我们这一代人受他们的影响太大了,完全掩映在他们的光环之下。这既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的负担,作为他们的后代,得到了更多人们的注视,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本文原载2013年9月26日《南方周末》)
(本文原载2013年9月26日《南方周末》)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