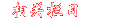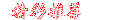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悼念晋绥老前辈毛大风叔叔(07月20日)
-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襟怀(07月08日)
- 一场别开生面的视频签约(04月30日)
- 林炎志:继续做好铺路石(04月27日)
- 黄河古渡黑峪口 “两弹一星”晋绥情(04月08日)
- 六百英灵—远方山中的牵挂(04月02日)
- 怀念老红军张文阿姨(03月29日)
- 想起贺老总在晋绥(03月21日)
- 虎年初春晋绥情(02月20日)
- 怀念“四八”烈士后代—秦新华大姐(02月16日)
我的伯父关向应
发布日期:2015-05-27 13:32 来源:大连日报 作者:关翠玉
♦作者关翠玉简历: 关翠玉 关向应烈士侄女, 1942年出生于大连市金县关家村,1960年大连市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工业学院。1965年毕业后参军,曾在第二炮兵研究所和军委炮兵科技处工作。1978年转业,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曾担任工业处处长、北京生产力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1999年退休。
我的伯父关向应,原名关治祥,1902年出身于一个满族农民家庭。祖姓瓜尔佳氏,原隶镶红旗,于康熙二十六年搬迁至金州,改为镶白旗。家境贫寒,靠耕种十几亩薄地和织布维持生活。伯父是爷爷的长子,由于他天资聪颖且勤劳、俭朴、好学,自幼便深得长辈们的喜爱。在伯父离家去上海从事革命斗争后的几十年间,老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病瘫在床的奶奶一提到他就落泪,在无尽的思念中去世。伯父逝世后,为了不让爷爷伤心,我们迟迟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所以爷爷始终盼望他的爱子归来。

关向应烈士
我们从小就看见家里挂着伯父的照片,爷爷常常指着照片里的伯父给我们讲述他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后来我立志从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事导弹研究,正是受了伯父的影响。如果伯父地下有知,相信他会为他所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为他的后人们正沿着他奋斗的道路前进感到欣慰。
一手好字,被称为“小代笔先生”
一手好字,被称为“小代笔先生”
少年时,伯父求知欲十分强烈,他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成了有名的高材生,受到老师、家长和乡亲们的一致赞扬。他在学校认真听课,在家里除了帮助父母干活外,就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看书、练字和学画,有时竟彻夜不眠。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就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春节或遇有红白喜事时,乡亲们就求他写对联、写文书,被村里人誉为“小代笔先生”。爷爷还告诉我们,伯父从小就知道替父母分担忧愁,六七岁便开始参加家庭劳动,放猪、割草、拾柴、耕地,样样都干。年幼的伯父很少穿新衣服,都是穿母亲拆翻过的旧大褂,母亲给他做的布鞋他十分珍惜。
贫困的家庭生活,使伯父在少年时就养成了朴素的习惯。16岁时他考入普兰店公学堂,伯父深知父母节衣缩食供他上学的苦衷,学习更加勤奋,攻读范围也更广泛了,尤其酷爱历史和古典文学,如《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古文观止》等,他都爱不释手。伯父一方面对劳苦大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1920年4月,伯父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这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18岁的热血青年。目睹大连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现实,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伯父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因为这是日本人开办的建筑企业,伯父认为中国有志之士不能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事当奴隶,于是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回家了。为此,爷爷还曾责怪过伯父。然而,爷爷哪里知道伯父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已经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宏愿,而他浓厚的学习兴趣也随之升华为追求革命真理的强烈愿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伯父只在家呆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就托人在大连泰东日报社找到了一份杂役性质的工作。在这里,他博览各种报纸杂志,广泛联系工人群众,探索解救中华民族的革命道路;在这里,他知道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认识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这里,他得以与党中央派来的李震瀛等人相识,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带来的《向导》、《新青年》等书刊,树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2月,伯父关向应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等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关向应烈士
不久,伯父离开大连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同时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和筹划赴苏学习。老实厚道的爷爷对伯父远走他乡很不放心,曾一再托人捎信叫伯父回来。可是伯父坚定地表示,革命不成功,决意不回家。赴苏联前夕,他满怀激情,写信给我的四爷,报告他去苏联的学习计划和报效祖国、献身党的事业的宏伟抱负。信中写道:“侄此次去俄,意定六年返国,在俄纯读书四年,以涵养学识之不足,余二年,则作实际练习,入赤俄军队中,实际练习军事学识”;“儿行千里母担忧之措词,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悟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反抗,此侄素日之抱负,亦侄惟一之人生观也。”这封家信纸短情深,表明了伯父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少年壮志。
与贺龙结下深厚的友谊
1925年1月,伯父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结束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深造,伯父回国后将马列主义理论用于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1928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年起,伯父先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1年,因中央机关被破坏,伯父遭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关押半年,饱受摧残。被党营救出狱后,身体尚未恢复,伯父便奉命来到条件艰苦、形势严峻的湘鄂西苏区,出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和红三军政委,从此与贺龙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两人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组合,让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一起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1939年,贺龙、关向应在冀中陈家庄战斗中视察地形。
伯父和贺龙伯伯一样,具有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他们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都记得,在洪湖时期,红二军团常与数倍以至数十倍于己的敌人苦战。如果说贺龙骑上他的大红马,擎起战旗,便是部队集合的标志,那么伯父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则保证了官兵团结一心,所向无敌。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他曾走到队伍中间对大家说:“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生就生在一堆,死就死在一块!”在长征途中,伯父更是在病中以惊人的意志,率领红军战士,与围追堵截的敌人、与极为恶劣的地形和气候、与饥饿及死亡进行搏斗,战士们从他身上看到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优良传统。他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打草鞋;将自己的干粮分给大家;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和战士挤在一顶帐篷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伯父把这种官兵亲密团结的精神带给全部队,他以共产党人的风范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官兵的爱戴。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伯父和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师挺进晋西北,后又转战冀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贺龙和关向应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被人们称赞为团结的楷模。中央军委发给他们的电报和他们发给中央的电报以及对下面的行文,常常写作“贺关”。贺伯伯的夫人薛明曾回忆说:“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在我面前,贺龙总说小关如何如何好,关向应则总说老贺如何如何好,言语几乎一模一样,从来没听到他们说对方一个不字。”可是,在1940年冬,一二○师刚从冀中返回晋西北不久,长年征战的伯父关向应终于被病魔击倒,肺病使他吐血不止。党中央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即决定让伯父回延安养病。贺龙得知伯父要去延安时,专程从前线策马赶往军区医院,亲自为他送行。
五千余人前来为他告别
1941年初,伯父病情稍有好转,便又返回了前线。此刻晋西北正是危难之际。他回去后,又没日没夜地投入了工作。不久,他再次吐血不止。在贺伯伯和党中央的再三催促下,伯父才不得不重返陕北,从此,便再没能从病榻上起来。1946年7月21日,伯父终于闭上了他的双眼。在他停止呼吸前的五分钟,他还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他一直是怀着活的信念挺到了最后。
当伯父逝世的噩耗传到晋绥前线,贺龙伯伯悲痛万分,泣不成声,难遣伤怀,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哭向应》:“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你先我永逝了,辞去了你亲手抚养的部队,辞去了千百万人民,还辞去了你的难友——云青(即贺龙)。整整十五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湘鄂边、黔、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起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我则寝不成眠……”
伯父在延安逝世时,才44岁。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的讣告,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提笔写下了挽词。毛主席的挽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这是伯父毕生经历的光辉写照。朱德总司令的挽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以志关向应同志千古!”人民群众写给伯父的挽联是:“永记心头,永世不忘。”
1946年7月22日下午5时,伯父关向应在中央党校入殓。入殓时,刘少奇、任弼时、罗瑞卿等同志均亲临视殓。23日上午6时,朱德、任弼时同志等将灵柩抬上灵车,各机关学校代表四百余人随灵护送,十辆护灵车徐徐跟进。当灵车到东关外飞机场墓地时,送葬代表及延安市群众五千余人肃立相送。朱总司令致悼词时悲痛地说:“关向应同志生平为革命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由于长期的对敌人搏斗,以致辛劳成疾。今天他死了,全党全军要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中华民族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
礼炮十二响后,伯父在凄婉的乐声中被安葬。蓦然警报响起,有两架国民党飞机窜入墓地上空,引起了送葬人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大都沉着而有秩序地散开隐蔽,但朱总司令、任弼时等同志肃然执铲奠土。中共中央办公厅及中央党校十余同志亦在警报声中完成奠土。伯父离开我们已经66年了,但在我们心里他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
(本文原载于《大连日报》2012年4月11日)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