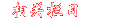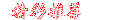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回忆》-- 家世(下)
发布日期:2016-05-20 15:15 来源:《我的回忆》 作者:晋绥基金会
我伯父的母亲辞世后,爷爷续弦后生了我的父亲,加上姑母,我的上两辈老人就有五口人。我先后有生母、继母共三人,我姐姐、哥哥的母亲病故后,父亲与寡妇结婚,这就是我的母亲,但我还不到两岁,她也病亡了,我的外祖父母为一直孝敬老人的女儿夭亡,从四十里外的家乡赶来哭丧,老人家是一位秀才,他给我起了个奶名,也是小名:“七七”。因为加上伯父母家的儿女和我的哥姐,我排名第七,他还另给我起了个名字叫“章汝”,我兄名叫“章儿”,我们这一代,我最小,前面堂姐叫“六六”,堂兄叫“五五”。继母兄姐七人,她名叫“八八”,因此以后不叫我“七七”,叫由外祖父定名的“章汝”。
我的亲生母亲亡后,父亲仍在商店脱不了身,爷爷已年老多病,我们姐弟三人更需要有人抚育,父亲为了子女不受继母的虐待,托亲朋好友找到一位心慈手软,又不能生育的穷寡妇,经人介绍,得到双方同意,这就是我的继母。她的哥嫂、姐姐都有2—4个子女,大部分家庭贫困,有的当长工;她从小勤劳,特别是婚后,为哥姐们照管孩子,学会了抚养婴幼儿的全套本领。姐姐比我大13岁,她的继母即我的生母死后,暂由她管家,给我解决吃穿,她为我这个小弟弟发育好,把我喂的肚子鼓大了,四肢细小了,两岁的人,站不起来,在炕上爬行也东倒西歪。继母来后,一天喂我六、七次饭,每次都不让吃饱,就是现在所说“少食多餐”。因为姐姐喂饭时我饱满惯了,不让多吃,使我哭声不断,爷爷每听到我的哭声,轻轻走到我和继母、哥姐们住的门外,后来知道不是继母打骂我;但伯母每听到我的哭声,就在院子里嚎叫,继母从不解释,坚持她的做法。父亲知道继母来后我哭叫比过去多起来,以为我这个小儿子受到后妈虐待,连着几天店里关门后回家了解真情,也是进大门后,先在窗户外静听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我的哭声,但听不到打骂声,回屋里后,看到我的脸色红润了一些,手足活动也较以前自如点了。我姐姐在父亲面前单独反映继母从没有打骂,只是弟弟每次要多吃几勺,继母总是哄弟弟,常说:“停一会儿再喂你吃”。父亲于是放心了,爷爷也高兴了。姐姐还因此把妈妈抱住说:“妈妈真好,我们以后都听您老人家的”。大概时间不太长,我不但会在炕上爬起来,而且自己可以站起来,还摇摇摆摆走着玩,并能较快的从炕上到地下。哥哥更是高兴,后来哥姐常对我说以上经过,我不但知道她老人家是继母,而且更觉得和亲生母亲一样互相疼爱。
继母的大姐病亡后,留下一儿一女,女儿名叫富银,她父亲即我表叔背着才五六岁的女儿走了六十里路送到我家抚养,使继母很为难,我父亲当天正好在家,就劝母亲留下富银抚养,直到十四岁时,家里来人把她接走,听说没多久就结婚了。抗战开始后第二年,距她家五里的柳林镇(今为县)被日军占领,富银与丈夫穆在光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到我们家,这是父母济贫扶危,人家也是又勤又强的劳动力,从此,跟我父亲、哥哥及两家男女老少(我已人伍不在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父亲和我兄加上穆在光共同种地,齐心协力,多打粮食,尽力支援前线。穆在光政治上,思想上一贯表现好,入了党。但土改时,我家被定为经营地主,穆在光被定为地主的狗腿子,开除出党,并把他全家(到我家后又生两个孩子)六口人赶走了。
在此之前的1935年,我已离家上高小了,在除夕之夜全家包括我新婚妻子薛秀明、我的哥嫂六口人正在包饺子,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脏脸长发,衣衫褴褛的男子,继母一下认出是谁了,马上大喊一声:“花狗,滚出去!”。这时我们也都看清了,是继母大哥的大儿子,我父亲马上说:“花狗,你快上炕来暖暖身子吧,看把你冻得浑身发抖。”并叫我兄马上去拿衣柜里我爷爷活着时穿过的棉衣,棉裤,同时叫我在院子喊对门邻居一位会剃头的人来给花狗理发。不一会,花狗的脏鬼样子变成清洁壮年男子了,继母还在流泪,口里还说“我真见不得人了”。头也不抬,父亲劝她放心,并说花狗会改过来的,我赶快到母亲身边,给老人家擦眼泪,她感动的把我抱在怀里,并说:“咱们家都是行善的人”。
吃过年夜饭,家乡人一般要过半夜后才睡觉,叫做“熬岁数”,我兄弟二人受父亲的嘱托,劝花狗改掉鸦片烟瘾,他满口答应,开春后种地很卖力气,确实戒毒了,但不到二年,偷我家的物品换的抽大烟。一天,在赌场偷一赌徒的羊绒围巾被痛打后,当即赶出村去,以后再无音讯,继母没有一点痛心表现,只是唉了一声说:“花狗从小就不是好东西”。我的亲姥爷是个秀才,他们家距离我们村四十里远,我一生在16岁以前只去过他家3次,第一、二次是二位老人家先后病故后我父亲领着我去吊孝,第三次是我结婚后,春节给舅父母拜年。我五岁生日时,二位老人来我家一次,除其他礼物外,送给我兔式帽子一顶,并有专用帽匣,平时把帽子放进去,逢年过节或走亲戚时戴上,大人小孩都围着看,1938年日军扫荡时被抢走了,继母老不忘记它。姥爷有3个儿子,有孙子孙女多少我不知道,他们都比我岁数大,小时见了还一起玩过。1944年初冬,县委、县政府举办冬学教员训练班,各区民教负责人也来参加,我与县政府民教科负责教育的科长共同负责,一天下午散会后,我在整理汇报材料时,五区分管教育的同志问:“你是冯家会的人吧?”我抬头看,他左耳垂缺失,马上说:“你是二姑舅哥吧?”。他高兴地把我的手握住说:“咱们亲姑舅兄弟,小时见过面,这次开训练班才遇到一起。”接着他说:“我叫薛隆祥。”他小时在村边玩,一只狼突然扑过来要吃他,他大概哭叫一声,把头拐了一下,被狼咬下左耳垂,此时恰好过来位壮汉,用扁担打在狼屁股上,狼逃跑了,我姑舅哥的命才保住了。这是我小时去他家听说的。五十年代初,在京召开华北地区县长会议,临县县长李汝民告知说,薛隆祥于1949年担任区长,不到两年病故了。
1936年红军东征前,一天中午,父亲所在商店柜台外一棵大柳树上,捆绑着我们村铁匠杨生明的前家子李拴弟,父亲看见周围没有反共军人,赶快近前,用抖擞的双手,把绑绳解开,把李拉进店里,让他从后门溜出去,并告诉他沿黄河向北快逃,走十里地有个大村子,村名叫索达干,住有防共军,从一条沟渠进去,上山后躲进土疙洞(农民在地里避雨处)千万不要回家。这个铁匠的儿子,是被防共军抓壮丁成为军人的,逃兵被抓住一律枪决,父亲冒险救了李拴弟的性命。
1950年,秀明的父亲病亡,经领导批准,我们把她母亲接到北京,老人家勤劳一生,还在院子的空场地种瓜种菜、我们的孩子上学都住校,学龄前的上幼儿园,寒暑假回家,我俩都上班,她负责照顾。 1952年的一天,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亡后葬于北京万寿路。
我的父母,也曾经领导批准先后来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第一次约在1953 年,父亲来了也种瓜菜,出门买粮食背回家,继母做饭、洗衣,也精心照管孙子孙女。但我父亲过不惯城市生活,老两口在一年半后回家乡了,不久,我继母病亡,族兄冯文堂大概觉得我父亲年老孤身一人生活太苦,帮功请去一位比我继母年岁还大的、但身体尚健的老太太,成为我的第二位继母。二位老人来京住了也是一年多,但是我父亲仍不习惯城市生活,又回老家了。
五十年代初,秀明三姐的大女儿陈玉珍曾来京住在我家,她学了护士,在西苑中医院工作。经人介绍,与军人殷洪业结婚后到兰州部队医院工作。八十年代中期,玉珍不幸身患重病,秀明买了药,不远千里送去,但很遗憾,也未能挽救,她的生命。她女儿在西安某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有时还来电话问候。
抗战刚开始,财东要把商店迁到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榆林,我父亲决意回家种田,正合财东之意;但财东提出:“你把几十年积蓄的钱拿来入股吧!”父亲把全部白洋五百元交财东了,不到半年,财东来信:“政府以商店严重偷税,把铺子全部没收。”这样,父亲辛劳几十年积蓄的白洋,白白被骗走了。这件事是老人家临终前才告诉我的。
父亲回家和我兄种地时,特别是1940年初,我党粉碎蒋、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家乡成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边区到农村,成立了政权。为了支援前线,村政府经常遵照上级布置的征兵、征粮等任务,村干部都要积极去完成,村公所有村长,无任何待遇,下属闾长,分管三四十户,我兄是邻长,分管十来户,因他能力低,胆子小,遇到困难话也不敢说,于是父亲替他执行任务,并还组织强劳力往前线送军粮。
我家当时已有土地五十多亩,但绝大部分土质很差,产量很低,为了多产粮、棉等农作物,父亲雇用了石匠和村里的好劳力来参加改造土壤的工程。地点在我家院子后边高山东侧的一条小山沟,沟渠两侧是爷爷和父亲先后买下的山梁薄地,占全家土地半数多,一遇瓢泼大雨,水土严重流失。改选工程主要是上下建筑坝堰两座,坝高约四米,宽六七十米,坝堰两侧有大水冲不裂的水道,可免去涝灾,旱涝保收。过去正常年景亩产三十斤上下,建坝后,亩产达三百斤。因农业收入明显增大,过去每年负担公粮由全村三百户左右人家的二十七、八位,后来上升到十三、四位。
1961年我奉命去吉林省梨树县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次年)1962 年秋初,接到姐姐(我兄文忠在几年前病亡)的电报称父亲病危。我请假经北京与秀明一起坐火车上路。到太原后,因秋雨多,土路不能走汽车,在太原等了两天,路还不通,真恰好碰到我们过去认识的碛口公社书记。他也急着要要回去,经打探,找到一辆急于开往临县县城的大货车,我们三人乘坐两天多,到达三交镇。已是天将要黑时大货车往北开要进城去,由公社书记向三交公社借来自行车三辆,经过曲曲弯弯,四五次扛上自行车渡过湫水河,于农历八月十三日半夜,才回到家里。父亲见我俩回来,高兴的翻身要坐起来,但很困难。姐姐和我俩抱着老人家,请他不要坐起来。父亲说:“你们盼六个孩子,上学、工作、当兵的都忙,苑苑在幼儿园,也不能请假回来吗?”我说:“路上难走,汽车不通.我俩从三交骑自行车才赶回来。”父亲听完我的话说:“我说呢。”意思是知道我们的难处了。姐姐给我说:“父亲在半个月以前还上山砍柴,准备冬天烤火。病下后,还不让请医生,说话到头了。”第二天我到碛口请来一位名中医大夫。他诊断后,把我叫到院子说:“没什么病,活到该走的程度了。”因此,不开药方就走了。我赶快请堂兄在村子里雇毛驴送人家。送走大夫后父亲问:“开药方了吗?”我答:“没有”。老人点了一下头。
农历八月十五日早上起床后,父亲的精神明显好转,穿好衣服,我姐姐给老人家洗脸,他说:“中秋节是咱小玉的生日,我今天不能死。”
过了两天,父亲要到院子里去。我和姐姐把他扶着坐起来,这时,我的第二位继母赶快给穿好鞋(这位老人大概也年过八十了),然后由我搀扶着走出窑洞。老人家仰头看了看太阳,在院子里转了约一刻钟,还上厕所解小便。我一直搀扶老人家回到窑里.三个人扶他上炕睡下。第二天,即农历八月十八日中午过后,父亲的双眼慢慢闭上,与世长辞了,终年八十八岁。我和姐姐失声痛哭。过了三天,举行了葬礼,本家族的男女老少,村干部,亲朋好友以及邻居们也来参拜,接着将老人家安葬在我家老坟地。二年后,族兄冯文来信说,在我离家时他主动承担照料我的第二位继母,现在她也病亡了,丧事已办妥。从此,我的长辈全部入土为安了。
2003年清明节,我儿子宏涛、小山回家乡,为我父亲立了碑,他们拍照回来让我看,总算了却我多年以来的一桩心愿。
哭父亲
婴幼饿病活生蛆①,童工煎熬星晨稀;
而立不惑为人贾②,耄年寿寝驾鹤归。
注:①苍蝇生的幼虫。②给资方作买卖。
挽母亲
生母生我病夭亡,继母养我累断肠,
继母生母都是母,今生今世永不忘。
写于生母诞辰一百周年,继母诞辰一百零八周年,一九九三年冬至节。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