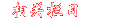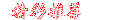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回忆》 被捕
发布日期:2016-06-14 15:18 来源:《我的回忆》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39年12月30日下午,县委书记贾英,突然到兔坂镇,并马上叫我离开四区到三区做更隐蔽的区委书记,还给我几份到岚县八路军三五八旅的领枪护照,供党支部直接组织领导的秘密游击小组使用,以便反击蒋阎的反共高潮。后来,我得知当时也把郭锡兰派到二区去了。我接受新任务后,马上到区公所请杨万选写一个到陕西邱陵受训(当时阎锡山躲避日军时,专事反共、破坏团结的特务分子训练组织)的通行证。带此通行证,准备掩敌耳目。我把通行证装入内衣,背上行李连夜行走近七十里,天将亮时,到达曲峪镇,立刻找到党支书,要他马上关闭牺盟合作社,免得敌人破坏,支书还叫新任村长给我抓差骑毛驴一头,动身沿黄河向南快行,这已经是当年的最后一天,行程七八十里到了堡子峪村,我要走山路,从毛驴鞍子上取下行李,赶毛驴的人说:“我家在招贤一带,也从这里上山,咱们还是同路。”我答:“你还是赶上毛驴快回家吧。”他把我的行李又放到驴鞍上,于是一起上山,走了十来里,到达我同学的村子一步堰,我又取下行李,给这一路赶毛驴跑运输的人3元纸币,当时只能买2两馒头,他一再推让,怎么也不收,并以感恩的口吻说:“我支差都由警察抓来运送,吃尽苦头,今天没挨打驾,先生也没骑驴,还给……。”我还是把纸币强塞进他上衣怀里。
进到一步堰村,打问清楚王敖的家,他正在院子,互相未问原因,在他家住了一宿。后来我才听说他与我一样,是派到四区,与他的村子相隔三、四十里地,就是四区所属的村子了。
1940年元旦天将黑时,我回到家里,父、母、姐、哥、嫂和妻子、儿子七口人,看见找背着行李,大概都认为无事可做回家了。吃完晚饭后,要我兄去请邻居会剃头的人替我把头剃光,同时,我对父亲说:“明天三交逢集,给我点钱,老人家马上从柜子里拿出每张一百元的纸币四张,我拿了两张,继母叫我妻子和姐姐翻一翻棉衣,他们拿到我父亲的棉袍大衣、棉袄、棉裤、棉鞋、布袜子,这样,我脱掉中山装,全部换成便服,父亲把毡帽也要我戴上。姐姐是织布、织褡裢的能手,正好有织出的褡裢六条,拿一块大白布包起来。我把贾英同志给我的领枪证平铺放进褡裢里。父亲的棉裤左右两侧的里边都缝制着暗口袋,我两张纸币各放一张,并把三区各村党支书的名单装进左侧的裤口袋内,与一百元纸币在一起。这时,我兄求村公所给我制好一幅白布印有印章的通行证,他去时,我把名字改称冯荣卿。
次日一早,吃完早饭动身时,父亲把一支钢制品漆棍交给我把白布包挑在肩上。行走四十里,到达三交镇,按县委书记讲的联络处,即我上高小的校址,去接应将直接指挥我在三区对敌做隐蔽斗争的县委民运部长成鸿猷(注:高小时的同学,头年全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的县委委员,1941年牺牲在日寇的枪口下)一见面,他问我回家时带书没有?我说:“不敢带”。他说:“我准备了几册,也不带了。”我说:“来时经过阎军驻地的岗哨,没有盘查过,带上咱还可以读一读。”’他一听,马上把已包好的灰布小包交给我。这样我在一根棍上挑上两个布包,自觉像个小商贩。他无法化妆,仍穿着中山装。动身时约好,我在前,他在后,相距保持五十米,如发生情况,我大声说话为警报,使他有机会躲避。我俩动身时,约是下午三时,出了三交,在湫水河的木桥两边有敌哨兵,但未盘查。走出三里,到达双塔村东侧文昌庙下,突然敌一哨兵用枪指着我胸前的通行证:“这玩艺不合格,跟我走。”我大声回答:“是政府发的,我到处通行。”我再三大声解说,敌兵就是非逼我照他指的方向去。我一直坚持到成鸿猷同志从我身旁经过,大约有六十多米远,只能看见他的上身时,我才不得已被敌哨兵押解上路了。当时我心里想:“完了”。走到进村子的木桥时,我准备跌摔下去,把证物特别是全区村里党支书名单和领枪护照等仍到河中冲走;但湫水河河水冻的挺结实,毫无办法塞进河水里。我脑子里很乱,只想到在临刑前的口号。然而却马上又想起一位地下工作者说过,不但要临危不惧,更要头脑冷静,才能从容对敌。真灵,我当时刚过二十岁的青年,办法马上有了。
过桥后进入双塔村,我被押进一个院子时,听见身后大喊:“报告连长,这人的通行证不对。”连长一摆手说:“押他去找保人!”我说,在这村里没熟人,连长一摆手,敌兵举枪逼我退出院子,在村街打问到曾在三交高小当过勤杂工的刘老师傅的门口,我叫了一声,出来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她听清我叫唤刘师傅时,回答说:“他父子三人到三交镇赶集还没有回来。”我一听,吓出一身汗,一点也没想到,时为县委社会部长的刘奋起和刘奋昭兄弟二人,都是共产党员,也都隐蔽在家里,大有可能危及这两位工人出身的先进战士的安全。当时,我马上冷静下来:“老人家,对不住,我听错人家的话了。”回头我对敌哨兵说:“我说过在这里没有熟人。”
敌兵把我押回连部后说,“他找不到保人,还没有搜身。”我心想,敌哨兵比敌连长刁,他大概非立功不行。敌人首先把灰布包打开,搜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科学概论》,《哲学选集》和成鸿猷的学习笔记本。当着这些证据,敌兵在其连长面前喜形于色。连长朝着我说:“你的事,我不能办了。”当即命令哨兵把我押送营部。营长一见这些物证,高喊:“完了,这么年轻的人当了共产党。”说完拿上这些书,命令两个士兵,一个拿步枪,一个带着冲锋枪,把我押解至团部。
一个自称团副的军官,当着两名押送我的士兵对我说:“同志,我是肖克、贺龙部队派来的,你把这里党员名单给我,我来保护。”敌人的骗术很愚蠢,我心里好笑,但表面上装着听不懂。但他用着急的口吻说:“同志,我们为共产主义牺牲是光荣的。”他老在主义上引我上钩。我回他一句:“老总,我是小商人,只有赚钱养家的主意。”他一听更急了,大声说:“不是这个主意。”停了片刻,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不是共产党,拿这些书做什么?”这一问,我准备的“口供”派上用场了:“我在三交镇四渠沟,碰上碛口镇大号商店晋泰祥少东家薛庭昭,他拿出这一灰布小包袱,托我带到他们柜上,他说还要到白文镇买麻。”我有意把二人说成各奔东西,相距甚远。敌团副截住我的话;问:“你怎么认识他的?”我答:“我常买他家柜上的货物,有时还有赊欠,自然……”他打住又问:“你怎替他捎这些书?”半天了,这个伪装的共产党员,才把要害提出来了。“知道包里的书是老总们要查的东西,我是不敢替人捎的。”我这样,软软地把他们顶回去了。
审讯完带书的事后,敌团副翻看成鸿猷的学习笔记,然后抬起头来问:“你会写字吗?”随手拿过一张白纸,一支钢笔。我说:“生意人,要记账,多少能写几个。”说完,我接过笔,左手按压着纸,以写毛笔的姿势,第一笔,就把纸抠开一道口子,他怕我把钢笔弄坏,一下把笔夺过去。他要我写字,企图查出铁证;我当时心里很放心,鸿猷同学写的字,全校第一,反证笔迹、书、笔记本不是我的。敌团副又问:“姓薛的是哪儿人?”我告诉他是下薛家坪人。(注:双塔村距薛家坪七里,距下薛家坪近70里,在黄河边上)这儿,又把距离拉大,让敌人难以为计。好像再没有审问追查的了,他喊来两个兵,叫把我关起来。那个抓我的士兵又来报告:“还没有搜他的身。”团副马上下令:“搜”。敌哨兵把步枪交给拿冲锋枪的,把我的棉袍拉开,伸手先摸棉裤左边的口袋,他大概摸得有感觉,问里边是什么,我说是钱,一百元的票子。他要我拿出来,我心里踏实了,一百元纸币和三区各编村党支书名单,都在棉裤左边口袋里,自己小心谨慎地只把钱掏出来。他一下手捏住纸币,问是多少,我说一百元。他又摸右边的裤口袋了。这时,我把一百元纸币仍装进左边裤口袋里。他又问,里边是什么?我回答:也是钱。他问:多少?我说,也是一百元。接着,要我掏出来。这边除钱外什么也没有,我马上掏出来,他又捏住问是多少。搜完身后,该团副命令把我关押在院内一小屋里。进去后,我把白布包放在炕上,自己也坐在炕沿上。进去时,我看见屋墙上贴着一张“马号”的纸,两个监视我的士兵,一人坐一个木凳子,两支枪对着我。不一会儿,那个哨兵走过来解开白布包拿出一条褡裢,对门口的士兵说,这玩艺剪下做鞋垫,冬天站岗冻不了脚,现在正是时候。敌兵的这一言,使我的心马上又跳出来了,领枪证会被敌人查出。但那个持冲锋枪的士兵没有表态,那个鬼点子不少的哨兵,把这条褡裢放在炕上离开了。我立即叠起来又包在白布包里,敌人也没有拦挡。我想,敌人以为处决我以后,褡裢可以由他任意处理了。
夕阳西垂时,我心里最着急,十分担心的是三区各编村支书的名单,在敌人处死我以后,仍有可能落在他们手里。当时想出一个办法,要求上厕所大便,乘机从裤口袋里掏出支书名单撕碎扔进大便坑里,后又打算撕碎咽进肚里。但押我的两个敌兵,也进入厕所,枪口仍对着我,便后仍关押原处。
过了一会儿,敌团副手托马列书进来,似笑非笑停下对我说:“你拿这些书走吧。”我当时明白了,敌人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马上说:“我不带”。他说,“这是团长的命令”,我去报告。过了片刻,他空着手返回来:“团长请你。”’我随后跟他进了原审讯我的窑洞。这个团长,看样子四十岁。他见了我马上说:“你还是把书带走,交还书主。”我仍以坚持的口吻说:“不带”。他诱导地说:‘没关系,这类书前些天在三交书店里还有。“(注:这话是真的,阎军阀的反共高潮前,我参加驻军与地方群众团体联席会议时,阎军会议桌上,还放着这类书籍)我还是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立即回答:“带上这些书连家也回不了了。”我以自私、落后的言行,不上敌人的当。敌团长说:“好吧,我开个单子,叫书主自己来取!”我回答:“一定。”这时,我背起白布包袱,一手捏着团长给的单子,扭头就走。敌团副看了团长一眼,团长点了一下头,团副拦着我厉声说:“我扣押你,不是为这些书,而是你的通行证有问题。”团长接着说:“找到保人,才能放你走。”
真庆幸,敌兵押着我走到街心,两位老农在我打问教员姓名后知道是我的同学王殿发刚从三交赶集走过去。按老人家指点的地方,我进了学校的窑门,一见到王殿发就朝他赶快用手指指着胸前的通行证,怕他喊出文耀二字来,证上是我的字冯荣卿。看神情,他一见就明白了,何况我身后站着持枪的阎军士兵。这时,我以恳求的口气说:“王先生,请开个保条!”开的是“兹证明冯荣卿确系本地人,如有不实,保人负责。保人王殿发。”(注:后来我见到时为区委书记的王敖,说王殿发当时已入党了,后改名为王子纪,后随我军进入新疆。)
敌人释放我后,夜里走了近四十里路,回家时,大约是半夜了。从家里人的面孔看,好像没有明显的惊吓情绪,我也没有说回来的晚是什么原因,也许因我来去匆匆,使他们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
从个人来讲,是一次经验教训。不化装,敌人以为是公家人;化装可以,但不应穿老人的棉袍,更不应该带上支书名单和领枪护照,其实带上杨万选办的去邱陵受训的护照,更会无惊无险。
次早,我到高家坪村,向成鸿猷汇报被扣捕后的情况,并把敌团长写的:“今收到冯荣卿交的薛庭昭的书四本,笔记本一本(后面写的是部队团号及敌团长姓名,我未细看,现在也记不得了。)交给成鸿猷同志,记得他也未看,马上撕碎扔进煮饭的火炉里,然后对工作做了安排和指示。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