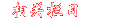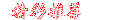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回忆》 土改(一)
发布日期:2016-06-15 16:35 来源:《我的回忆》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五四》指示,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合作时期,临县党以当时合法的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发动农民实行减租减息, 1940年1月建立人民政权后,又经六年多的斗争,广大贫下中农的土地基本解决了,只有极少数贫雇农缺地和缺好地。
1947年3月康生带一批干部到临县搞土改试点 我们十分高兴,都认为这是全县人民的一大好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他带来的是祸。态度蛮横已是小事了,他那疯狂的极左,真令人难以理解。先说一件小事,他头一天晚上到达,在途中吃了晚饭,县委准备的早餐,是牛油茶干馒头(俗名“到口酥”),专请大饭馆的高手帮着做的,县委书记樊不屈负责给康生端上,我负责给曹轶欧端上。康生发了脾气:“我的牙口不好”。曹接着说:“故意整人”。这钉子一个赛一个硬。我们俩立刻退出来,但马上一想:饿着他不得了,随即进去请教:什么饭适口,我们还可以重做。”他立即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要享福的。”这话更刺人,别人倒里外不是人了。我们只好又退出来,向他的秘书凌云打问什么样的饭合适。人家回答:“不知道。”这一回答使我们手足无措。县委生活干事成秀山说:“煮挂面下鸡蛋。”家乡也叫鸡蛋挂面汤。煮煎好后,我们仍一人端一碗送给坐上客。他们端起来吃了。饭后,我们向他汇报1938年开始减租运动到执行“五四”指示的过程和结果,使封建所有制的土地,绝大多数转移到农民手里,当时只有很少的贫下中农缺地和缺好地。
看来康生根本不相信事实,在听汇报过程中,几次责问被他贬为右倾、原为分局书记的张稼夫同志,并指着我们说:“你们这个党不是土改的党。”这样,康生的鞭子,从上到下,打在坚决并正确执行党的土地政策的党组织,从此。土改运动在临县变成康生一个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后果如何,历史有见证。
当时确定康生试点的是五区郝家坡,在他身边的除了临时秘书凌云同志外,还有张稼夫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等同志,以及临县县委书记和县长,把我留下主持全县的日常工作,也可适当参加土改。当时我虽对康生的蛮横不太理解,但我因未能得到在这样高级的党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而好好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而感到有些惋惜。
康生带领人们到郝家坡村,首先一口否定了晋绥分局制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提出不能只看剥削时间和剥削量。按照他的精神,土改工作就开始把只有轻剥削和剥削时间很短的农民,也定为地富,打击面由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左右,扩大到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他带着的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在郝家坡附近二三里的村子也搞土改试点,差不多都照他的一套试点。实际上没有试,而是整个就照他的一意孤行办了。过些天,试点扩大到白文镇。时为临县县委委员、贸易局长的李士彬,其祖父早已去世但被定为破产地主。当时人们把这种做法称为“查三代”。一天,我从乡下回城里,路过饭摊子时发现李士彬的大儿子海源和二儿子广源两个小男孩,正面黄肌瘦地伸手向吃饭人要饭吃。我刚进县委,民政科长孙廷铭向我讲:“县长可能怕连累自己,通知我停发李士彬家属的口粮和菜金。”他这么一说,使我明自刚才亲眼看到情形是怎么回事了。李士彬夫妇都是革命干部,当时按政府规定给孩子们发粮票和菜金。我说:在旧政府时,对死囚犯的处罚都没有饿罪和冻罪。即使孩子们的曾祖父是地主,甚至祖父、父亲是地主,也决不能叫孩子们饿肚子。我说。一定给他们照发生活费和粮票,责任我负。科长说:“向你汇报,就是要求发,并一定补发。”我说完全应该。
现在看来,康生不是来搞土改试点,他是要显示独出心裁,苦害良民。他到临县前与陈伯达共同起草了《告农民书》,其中有一句“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并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以粗黑体字刊出。1947年 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委驻扎在临县双塔村,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一句文字后,有些不太理解,于是去向他请教,这位有光辉业绩的卓越领导人,在听了我的反映后,顺手拿起《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读了几句,我记得其中有:“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推动运动前进,在理论方面比其余无产阶级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结果,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共产党人的理论丝毫不是某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的思想为依据。”我的水平很低,但听了以上论述,更觉得康生等的“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符合党领导农民实行土改的原则。事实胜于雄辩,当时很快出现了不仅打地富,更多的是打干部,打保护干部的党员和贫下中农。在康生所试点的村子第一次出现打人的事,干部、党员 当即提出:“只能说,不能打。”康生马上说:“打几下出出气。”从此乱斗、乱打,有的被吊起来,等等肉刑,打死不少人。
一天,在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把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扒光,平放在铺着煤渣的地上,由四个壮汉抓住手脚,来回推搓,磨破了刘妻的脊背。在将刘妻衣服脱掉扔在地上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但在场的人们不知伺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他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等他们的政权来了,反攻倒算。”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出埋藏在地下的白洋,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干部子女也在劫难逃,如家在县城南门外的李树藩,时在县政府民政科当科员,出生前父已病亡,生前有些轻微剥削,以后只剩母子二人,其母辛劳养育其长大成人,参加了革命,结果被定为地主,也把李押回去吊打了几次,逼其母子交出地财。干部家庭定为剥削者不少人也被逼迫过,,就不再举例了。这一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康生还从其“发现”的地财决定了没收工商业,几乎不分青红皂白,没收的所剩无几,极大的破坏了当时初步繁荣的工商业。
康生在临县土改试点的极其严重的极左路线,破坏了党的正确政策,本来“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就可能被坏人利用,再加上康生以上的“发现”和“发明”,又多害死了不少人。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的乱打乱斗的严重情况,把本来正确而又必须的土地改革运动给搞乱了。
家乡不幸来恶棍,康生害人走红运,
天灾未来人祸凶,致死无辜数百人。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