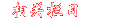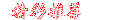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回忆》下放(二)
发布日期:2016-06-23 10:15 来源:《我的回忆》 作者:冯文耀
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造成严重后果,在农业方面,粮、棉、油料、猪、鸡及大欠牲畜等比1957年大幅度下降,各类产量差不多是1951年的水平,使城市和工矿区域粮、副食供应紧张,农村缺粮户也不少。1960年夏,我去安徽省招生时,去探望部里和学校下放劳动的干部和师生,除二、三人因在农业中学代课能吃饱外,其余人都浮肿。我出差前因浮肿一次住院,两次去外地疗养。这都是领导安排的。去后,公社请我吃饭,也邀请下放同志共餐,散席时许多同志说,这一顿饭可吃饱了。
中央决定对工农全面调整,发出《农村六十条》,纠正忽视农业(大炼钢铁也挤了农业)计划经济。1961年6月,中央决定从中央党政机关抽调周三百名司司局以上干部到大跃进前三百个棉粮高产县帮助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时副部长冯铉约我谈话,征求意见说,部里想安排我下放农村四年,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我马上表示服从并坚决同意。他还解释说,部里原先没有考虑你去。你曾下放劳动过。但因部里过去做过农村工作的的同志,只有你和伍宇,他现在国外工作。我再次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自己还真想再做一次农村工作,特别是下放遵化时间太短,但深有体会。
这批人出发前,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会的只有一百三十多人,其中高级干部只有胡耀邦一人,另一位是铁道部部长助理。首先听刘少奇的报告《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报告中分析了当前情况,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讲了总体方面的政策等。接着时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讲农村经济的具体政策等十分引人重视的办法和措施。他说,应当适当的给农民一些自由,如养猪、鸡、鸭等,允许搞些家庭副业,开垦荒地,种好自留地,并提出可以搞责任田,并说包产到户并不是单干,对居住分散户应允许单干。我听了心里有了底,这与下放遵化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很相似,这次可以去经过实践,完成党给予的使命。
我被分配去东北,首先到沈阳向东北局报到,去后,东北局让我们先参观鞍山钢铁厂等企业,然后分到吉林省,见到省委第二书记赵林(土改时为临县土改工作团团长),他向我介绍了农村情况并做了指示。同时我也看望了时为省民政厅长的高闻天,他是解放西北后从部队转地方工作(在本文土改一章中,我讲述过高的遭遇和赵林如何依据事实和政策正确处理的情形)。两人久别重逢,都很高兴。高还邀请我去他家吃家乡饭,他的爱人宋桂莲亲手做的饭菜。吉林省委决定我去四平地区所属的梨树县工作,但要我自选参观处。我选择吉林市,因为我老上级毛诚大姐是吉林市委第二书记。有人说省委原任命她为书记,她自己坚持这一职务。我想顺便去看望她。见面时她劝我既要坚持原则,又应讲究方法。大概她听说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她还告诉我一件事,大跃进时,流经吉林市的松花江水变得混浊,周总理发现后了解到是上游突击建立四座化肥厂所致。总理立即下令将化肥厂关停,此后,松花江的水又变清了。我参观时住在该市宾馆,服务员介绍说,我住的房子周总理曾经住过,比这高级的房子他不住,饭菜他自己定,担心接待处把伙食质量提高,亲自到厨房去查看,还与炊事员交谈。大家为总理如此平易近人而深受感动。
我到梨树县前,先去四平地委。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地委负责人要我传达刘少奇、邓子恢二同志的报告。这中间他去接电话,当他回到会议室,我将刘少奇的报告已经传达到尾声了,他在我身旁耳语:“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邓子恢的报告有问题,是修正主义,富农路线,不允许传达。”以后,邓子恢同志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
我被分配任梨树县委第二书记。这个县地处松辽平原,中长铁路贯穿其间。大跃进前,该县每年征收公粮一亿斤;但困难时期不但不能给国家粮食,而且还要吃返销粮三千万斤,人吃喂马困难多了,饿死了些活大牲畜。农民吧活着的用绳子吊起来。他们对我说,这样可以等到使它们维持生命的时候,要不饿的卧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当时东北地区生产力中主要靠大牲畜。因此,农民十分重视大牲畜的存活问题。
我到梨树县不久,县委书记马鉴要去省委学习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民主集中制》。走时他给我三份干部材料,叫我主持常委会讨论并作出决定。常委讨论通过后,我对组织部长常委贾天才说:“等老马回来看看再发文件。”他回来后我汇报了讨论结果,并把文件给他审阅。他马上板起面孔说:“那不行!”我重复一句:“这是受你委托常委通过的。”他提高声音说:“那也不行!”好一个第一书记,刚学完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竟然推翻他授权常委会议作出的决定。对这种专制作风我也领受了不少,见怪不怪。过去在家乡和进京工作,不也遇到过这样的表演吗?许许多多本可以办好的事,却往往被此类专横者给办坏了。
当时的梨树县委县政府办公楼挺宽敞,县委常委、正副县长,都住在有暖气的平房。1963年初,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就是“四清”运动,县委书记要我同他到一个公社搞试点,当时还天寒地冻,叫我带队先去,说他有事一时去不了。我去后发现冬季积肥太少,太干、都认为应该补救一下,于是我就同大家一起组织社员突击积肥等备耕工作。十多的大力积肥,便了解到干、群的一些思想问题。积肥成绩显著,社员队干部高兴。后来,县委书记来了,他说:“怎么‘四清’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多少呀?”这话也符合事实,但我坚持说:“如不大力抓备耕,难以丰收。”两人意见相持不下,我把争论向地委第二书记汇报了,但他没有表态。1964年要调我回北京时,这位同志对我说:“当时你是对的。”我说:“是与非,是否对党的事业有利,对当起什么作用,不是个人说了算。”他说:“问题就在这里。”
总的说来,当时党的风气是好的,特别是党对农村的政策宽松了点,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虽然遭受了当地历史上少见的大旱,县机关领导和干部大部分时间在乡下,组织领导并直接参加抗旱,使旱情逐渐得到缓解。当时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去,看到干群一起抗旱的场面,赞不绝口。他还握住我的手说:“在沈阳,你也不多住几天,多参观参观,急着走了,为的是把生产搞好。”当年梨树县农业总算丰收了,不仅在返销粮上没有向国家伸手,而且还提供了商品粮五千万斤。
二年间,我接触面不广,也不太深人,但也感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特殊化的风气。如我第一次下乡,李憬和我都背着行李已走到火车站(县所在地郭家店是中长铁路的火车站),突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面前,司机下车对我说:“冯书记,下乡时常委同志都得车接车送,上车吧!”我说:“我们去郭家店,那里也是火车站。”司机又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接送你们。”我和李憬还是坐火车走了。上火车时,看见司机仍然站在吉普车前来动。后来还遇到一件事,一次,通知我们去看戏,没有发入场券。县领导和我俩到剧场门口,检查员不但不收戏票,还点头让进。一般干部和群众把这叫做“点头票”进入剧场,看见前五、六排正当中空着位置边还站着看空位的人。一看便知这是专给领导占的座位。这一风气,下放遵化县时也遇到过。这一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后通知看戏看电影,我和秘书提前走出办公室,想看的话就自己买票,不想看则去逛大街。后来觉得这种消极对待也不对,于是就在一定场合提了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此风当时也就改正过来了。但用吉普车接送的做法没有完全改过来。梨树是个产粮多的地方,县粮食科有运粮汽车二、三十辆。下乡前我俩先打听何时有车去何地,我们搭乘运粮大汽车,对这一办法我也曾提过建议,并指出县委县政府才各有吉普车一辆,如果大家都用吉普车,就会影响应急下乡时的需要。有的同志后来也照我的意见去做了。
梨树县有极少数大队在山上,这些村子一般是土质差又缺水,生产收成难度大。其中有一大队名叫团沙子,我第一次下乡到这里,正与大队干部下地干活,大队会计来通知:“马书记在做报告,要你到大队部电话上去听。”我赶快放下农具去听了。这种情况,遇到过三几次,我原来没有想到当时有这样先进的电话可以听报告。
1962年冬天征收公粮时,我正在一公社吃晚饭,县委书记来电话说姚家大队征公粮有问题,叫我去处理。到该大队虽只有五里路,我和公社书记到达村里时,天已大黑,问一社员支书住处,他说往前瓦房院就是。月亮出来了,进去一看,院子挺大,足够一亩地的院子,有瓦房五问,我们当晚就住在支书家。当地农民许多是两户甚至三户住一间大屋,质量差的叫“马架子”,大屋子有两盘炕,有的一盘炕住二户人家,有条件的户与户之间用衣箱隔起来,下乡干部晚宿也挤在炕上。话得说回来,第二天睁早饭时,一盘炕上摆了两桌,一桌四人,每人一只烧小鸡,每桌还有一大碗鸡蛋羹,一大碗东北人冬春爱吃的酸白菜和其他炒菜。困难时期这样的名菜早餐,支书的用意,我和公社书记都意识到了,我俩耳语商量决定,由我宣布:“今天早饭,我和公社书记老常每人出菜钱两元,交粮票半斤,谁也不请谁的客。”回到县委,我马上告诉给纪委书记,他派人调查后汇报说,大队账上记:“招待县委冯书记八十二元”还查出过去招待上级领导人就捞了三百多元。
征粮出的问题,也在支书身上,他家的产量报的很低,评议小组不敢评,我们只从群众口中秘密知道,叫积极分子评产,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1963年,毛泽东批示要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规定劳动比例。县委较重视,县社干部大都带头参加义务劳,对大队干部特别抓得紧,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了成效。我和李憬还分头专门调查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情况。社员说,干部过去是“少劳多得,不劳也得,现在好了。”此后干部参加劳动的逐渐多起来了。因此,却曾鼓励了社员三产积极性和丰产丰收的信心。
1964年5、6月间,吉林省委组织部派人征求我的意见,要把我留下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六月通知我提前一年回北京。离开前,县委给我做鉴定。在会议上大家预测当年可能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六、七千万斤。看来只要不再瞎折,再经二三年的努力,恢复到“大跃进”前的一亿斤是可能的。当年七月底回来后,邹大鹏同志对我说,“吉林省委经中央组织部向我们征求意见,要留你在吉林工作,任四平地委副书记。但正好学校要扩大招生,以后本科要年年不断招生,学校任务加重了。经中央组织部同意,就决定提前把你调回来了。”之后,我请邹部长审阅了梨树县委给我做的鉴定。
梨树县委给我做鉴定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讲,生产小队一般四、五十户,不少社员反映,小队规模过大,管理困难多,干起活来“大呼啦”,你看我,我等你,劳动效率低。因此,我虽经几次建议,人家不理。因此走时,做为最后一次建议:“小队二、三十户为宜”。一把手仍又一摆手,表示不同意。
最后补充一点,下放时根据中央规定,可以在单位内自选秘书一二人,一同下放东北。我决意带一人,不自选。组织上坚持要我提名,但我提了两位,都说工作离不开。在无奈之下,我只好提出:“那就只有李憬了”。我并非不愿意选择李憬同志,而是1958年下放河北遵化西下营劳动锻炼结束时,我起草的《调查报告》是李憬代抄的。反右倾运动时,也批判过他。因此我不愿在这次下放工作时再选他当秘书,唯恐发生什么事情牵连他。
没想到还没出发就遇到点儿麻烦。临走前,召开部务扩大会议,部党委委员(我也是党委委员)也参加。发言的部、局领导同志大多讲了些建议,希望等临别赠言。一位女同志,曾经在干训练班学习过,她以质问的口气问我:“你在遵化反对人民公社时,几乎跟李憬结成反党联盟,这次下放,又带着他当你的秘书......”她的话还没有说完,主持这次会议的冯铉副部长高声说:“你想干什么?”一句话制止了她的盛气。前几天(2004年7月3日),在院子散步时,一位同志告诉我:“要不是当年你把李憬同志带走,他会被开除的(大意)。”据说,又是那位女同志为此在机关有过活动。到底是要开除党籍还是开除公职,我没有多问。
李憬和我又一次下放,我俩共同配合工作,有时为了多了解情况,我不是总把他作为秘书带在身边,我们有意识的分别去不同的地方,尽可能多做些调查研究。我们先后向中央写过十次调查材料,回京时把材料交给梨树县委了。我们回来后知道,与李憬同志同等情况的干部,在我们下放期间,都提升了一级工资,唯独他的级别未动。他是1949年秋初我去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调来的青年干部之一,是位好干部,对党一贯忠诚,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能力强,文笔好。团结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下放时,东北天寒地冻,得自己买皮衣等御寒服装,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他于八十年代任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副书记,现已患帕金森病几年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伴不幸于多年前意外身亡,子女忙于工作,现在靠保姆照顾。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 本站编辑:姚文君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