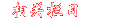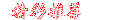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我的回忆》文革(八)
发布日期:2016-06-28 15:19 来源:《我的回忆》 作者:冯文耀著
1975年10月的一天,赵一之对我说,你被分配到唐山河北矿冶学院,今天就动身。当时大部分同志在一两个月以前已被分配到河北一些市县学校去了,个别同志分配省机关。我路经保定市时天已黑了,就住在已先分配去的同志处。次日登程,路经北京,在家住了一宿,第三天到唐山河北矿冶学院报到。时为党委书记、院长的张毅同志一见就对我:“省里决定,你可列席院革委会会议,日常工作和党的生活,就在教务处。”这样,我总算有了工作。当时的处长吕方润,是教授还在上课,副处长是季祥,两位都共产党员。我要求多给些工作。院里有时也同意我随一部分师生去农村、工厂参加开门办学。
1976年1月9日早晨,在广播电台突然听到哀乐,原来是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并十二万分敬仰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我痛哭失声,早饭也吃不下去。写到此,我又悲痛起来了。过了几天,张毅在会上提出:“省委党校要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学习班,要我院去一名副院级以上的人报名参加。”半天无人说话。我提出“如果允许,我去学习”。马上得到同意。当时河北省委党校在保定市。当我路经北京时,正值为周总理的逝世召开追悼大会。沿途都听到哀乐,我的眼泪止不住往外流,心里默念:敬爱的周总理,您安息吧!当时火车里的人都站起来默哀。
到省委党校后,饮食也挺困难,炒菜无味,人家老熟人问炊事员:“菜是什么油炒的?”回答:“水”!这也从一个点反映了文革对生产影响之大。
对毛选五卷,我从头到尾读了三遍。1955 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是符合国情的,符合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以后的论文、报告和有些批示,虽然批左也批右,但批右时把中央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的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到三年,就批别人“像小脚婆娘走路,东摇西摆。”(批评周恩来,但未点名)文章指出:“当前是合作化高潮,一般是半社会主义,也有少数是社会主义的高级社。”学到这里,我才知道 1959年我下放农村劳动时,有的老农反映:“初级社刚办起来,就大办高级社,两级社办起来不到六年,这……这……”他说不下去了。大概他想说:公社化的路子走得太快了,没有说出来。1953年6月15日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文中,批判左的急躁情绪后,批判了“确立新民主义社会秩序”等三种右观点。文章的结尾论证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国情。这一段论述是:“我们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我在学习时想,如果照此把农业逐步过渡为半社会主义,如果不是重点批右,1958年的全面大冒进不会出现。即使有些地方有些方面出现了,也可能头脑冷静,听得进不同意见,加以适当解决,不会造成经济大困难。基于我有以上想法,在学习中,我没有写笔记,也没有发言。
“文革”末期,由毛泽东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他听了侄子又是贴身联络员毛远新的耳旁风。说邓小平对“文革”的批判,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1972年周恩来正确地领导了批判林彪等人的极左,毛泽东却说应该批右)江青等人本来对周恩来因病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怀恨在心,乘机煽风点火,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要算“文革”的账,包庇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刘冰请邓小平转信,状告江青帮里驻校宣传队头头迟群、谢静宜的问题。)信中提的问题,“矛头是指向我的”。这样,从1975年11月3日以后,把批邓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把刚刚好转的形势,又推进了深渊。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瞬间,整个城市变为一片废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全市原有107万人口,震亡22万多人。我所在的河北矿冶学院(今改名为河北理工大等失伤亡尤其大。原有师生员工及家属3602人,震亡1247人;全家人员遇难的有72户;家属遗孤26人。所幸当时还有200多名师生在农村开门办学。否则死伤更多。特别是学生,住的是集体宿舍,一居室住十数人。学生伤亡比例比教职工大。当时的伤亡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活着的人,守着罹难的亲人,悲痛无泪。党委书记张毅和副职的孙德水、耿庆钧都震亡了。副书记梁友珍和程浩幸免。程浩全家三男下来。震时他正外出疗养,震后带病速赶回;大儿子程阳泉在石家庄上大学;小儿子程清泉在家震伤,被好友救出;老伴和两个女儿都不幸遇难,家里还着了火。原国际关系学院经河北分到矿冶学院的童林夫妇均未能幸免。原国关到河北唐山的男女老少九人,震亡三人,活着的六人,其中二人是震前头一天离开唐山回北京的。
我于头年到唐山,住在老宿舍楼靠大街的一层。邻居说,这一带不太安全。这座楼的房顶是瓦料的,后把楼顶换成整块的石棉瓦,虽然地震震度很大,但它没有马上上断裂。因此,住在这座楼的大人小孩地也震时有一定的时间逃离出去。地震刚开始时,我梦见坐在疯牛车上,东摇西歪。此时,老伴推我一把说:“地震了。”我醒来时从枕下拿出手电筒打开看见屋顶后侧二楼人家的衣柜,有多一半悬在我家的屋顶上。我俩马上躲在窗户口旁。突然一声巨响,南墙连门带窗朝外倒了。我说:“给出路了。”1968年毛泽东为《红旗》三期写编者按语中提出过“给出路”三个字,寓意给一些曾被打倒的,关押的领导人出路。
我俩逃出后救出来第一人是二楼衣柜露到我们房顶下的的人,她是开滦医院的大夫。同时发现梁友珍也从房里爬出来了。当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宿舍院子里只有我的手电,拿着它照明,协助梁救人。不少逃出来的人也主动救人。我俩组织几批人,抢救被压在废墟下不能自拔的人。然后把救出来的重伤员抬放在安全地方。我老伴用力扶助轻伤能走动的中老年妇女往安全地带送。当时接连不断发生余震,在救人者中,有的因余震而伤亡。我家二楼邻居夫妇都是老师,当晚从北京来一亲戚,是个初中女孩。男老师先把亲戚救下来,又上去救自己被瓦石压住的女儿,但不巧发生了6.3级余震,结果父女俩人都震亡了。还有邻居家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原也被压在碎瓦砾下,当我们组成抢救人上去时,被余震砸得血肉模糊。这座楼的东侧,住着时为教务处正副处长。处长吕方润伤势轻,没有转送外地;副处长季祥腹部伤势很重。我和三个中学生把他救出来要用汽车送机场时他说:“老冯啊,我不行了,你还是救别的同志去吧。”我们坚持送他上了飞机。后来知道他被送到太原,不但救活了,而且没有残废。矿院校庆四十周年时,我应邀去唐山。此时,吕方润已经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吕方润和季祥现已年过古稀,身体还很健康,去年还捎口信问候。
我们这座楼震亡43人,是全院最少的。最多的是学生宿舍楼,有的楼震亡280多人。我们先是就近救助本楼的伤者,接着又组织力量去营救其它楼的幸存者。刚到一座楼下,听到一个女人不高的凄惨哭叫声。几个人从废墟中爬上去,发现她被一大块水泥预制板压着。我们用尽气力抬起水泥板后,她哭着说,身下已死的是丈夫。这位男人是刚调来任武装处长的转业军人。
地震毁坏了水、电、通讯和铁路交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在京都有亲属,但死活消息传不出去。当时,生活用水主要靠部队汽车来送水(地震两天后部队来了),大家排队可以领到少量的水;燃料则用震坏的木器家具和破窗户;吃的主要靠由飞机空投,如烙饼等熟食品。当时,整个震区许多人吃不饱,去震倒的食品店“偷”点东西,据说有人乘机抢。
从凌晨到午后,活着能动的大多数人集中力量救助震伤者,但也有个别人怕余震,装病躺下哼哼。我老伴在空场上捡到一块从飞机上扔下的馅饼,我正饿得难受,因为早、午饭没能进食,拿起来放在嘴上,才发现假牙没有戴上,于是回到住处去找,当时还有余震,我放大胆子爬过窗台,进入地下,半天发现上口假牙全被震碎了,下口假牙在废墟堆旁,还没有碎。但一半假牙,无法咬食。老伴只好专门给我拌疙瘩汤,我则往下吞咽。当时因劳累过度,饮食困难,产生浮肿。累了不能坐下,休息完了,又站不起来。对此,应对的办法累了休息时,上身靠在大树上,等缓过劲来,移步向前又可去救人。
唐山地震后,时任代总理的华国锋去还有余震的唐山了解灾指挥:赈灾和震后重建等工作。灾区干群深受感动。唐山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在部队的支援下,一边救人,并掩埋、消毒处理遍地已腐烂散发乏出臭味的死难者尸体,一边抢搭地震棚,防雨、防余震。但就在此时,江青却高叫:“东震西震,不能停止批邓”。唐山地委书记遇难了。活着的地委领导人,哪敢违抗她的命令,只好召开还活着的地市级干部,开展批邓运动。
一天,突然有人喊:“老冯,好不容易三天才找到你。”当时我正跟三个青年把刚从深坑里救出来的伤势很重、身材高胖的中年妇女抬着往汽车上放,我一听并扭头认出是铁道兵某团团长薛玉福。他又说:“要不是先看见她(指我老伴)领着我,见了也认不出来了。”当时我剃光了头,只穿着背心短裤,脸脚浮肿,多天没有洗脸,满嘴没有牙,难怪人家不认识了。他是从北京带部队来救灾的,问我:“你要什么?”我说:“手电,我的手电在救人时借出去了,当时天太黑,我认不出是谁,大概人家也不认识我,也没有功夫还。”他马上从挎包里掏出手电给了我,接着问我还要什么,我说:“烟压在房里了,现在也无处买,手里也没有钱”。他叫通讯员拿给我香烟一条,火柴一盒。又:问我还要什么。我说什么也不要了。但马上问他:“你们最近有人回北京吗?如有人回去,,替我给孩子们带封信”。他说:“正好通讯员明天回去”。我马上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两页纸,,用他的笔,给当时在京的三儿子写了一封信。
又一天,也突然来了原国际关系学院青年教师李树山。一见,他把我抱住,并说:“冯铉部长特派我打问你。你真命大。”我当时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冯铉同志原也是调查部副部长,“文革”中部里军代表等原打算把他编进“五七””干校到农村劳动改造。周恩来同志得悉后,把他调到中央联络任副部长。前文提到,1959 年反右倾运动,我是部里唯一受到批判的重点对象。批判会他都参加,但从未发言。一次散会后,他劝告我“检讨应简单些。”1962 年中央要抽调司局级干部三百人,到原来三百个棉粮高产县,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找我谈话,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响应党中央号召,到农村工作去了。
当年 10月,救人救灾完成差不多了,我请假到京配牙,但做牙排号已到次年三月了。可巧遇见老战友胡克实(原在我县任县委书记,后为共青团中央副书记,当时任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因赞同胡耀邦的《汇报提纲》即在科学院任职时向中央写的报告,被作为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范围,正在受无端的批判)在家里闲着。他认为我是灾民,又需要尽快赶回灾区组织相关震后工作,于是就托邻居一个在牙科当助手的女孩子帮助挂上了号,这也还用了两个多月才做好。
在北京做假牙期间,当时调查部从“五七”干校回京的大多数干部住在国关,大家看到我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真命大”。有的同志说:“部里的赵礛同志震前出差到唐山不幸震亡,部里派人料理丧事时看过你吗?”’我对此一无所知。
唐山大地震,使我远在西藏的战友郭锡兰和青海的刘枫二同志寝食不安。郭锡兰与在京的战友苗志岚通信,得知我在大震中连伤也未受,他回信给苗时,附诗一首:
惊闻唐山大地地震,幸吾挚友命尚存;
不顾危险救难胞,昔日楷模今英雄。
我回到唐山后,学写了《和战友》一首:
风云莫测天地惊,在劫可逃命尚存;
生为人民当奉力,战友过誉心不宁。
郭锡兰时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因劳累过度,不到古稀,病亡于北京。刘枫同志也早逝了,亡前为西宁市市长。
我在北京做假牙时,大女儿从河北承德兴隆请假去唐山。当时,原学院政治部保卫科长李荣兴远道从仓州到唐山看望我,他曾一再表表示要动手挖掘我家中压在废墟下的东西。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我女儿再三劝阻,才未动手。当时在北京工作的二儿子出差在上海;大儿子在农村劳动;小女儿在西安军医大学学习;小儿子在部队服役。前文说,当时在京的只有当工人的三儿子。前去唐山震区探望我的还有一些人,如原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生、原国际关系学院分配在河北一些县工作和当教员的,原六五届本科生袁保安,经常去帮助干一些脏活累活,并还给我在地震坍塌处和防震棚前拍摄了照片,以做纪念。
我的假牙重新安装上后,准备第二天返回唐山时,从“五七”干校返京的原调查部干部局长王珺告知我:江青一伙被抓起来了。我高兴得通宵未眠。这是叶剑英又在党的重大历史关头,经与华国锋以及周恩来力保下的老革命家们共同做出的特大功勋。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姚文君)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