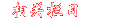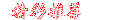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庚申忆逝(13-14)
发布日期:2016-02-15 14:51 来源:《庚申忆逝》 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 三
我从延安回晋西南不久,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阎锡山在秋林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所谓“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长、师长、旅长等高级军官,各区专员和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干部,一部分县长、公道团长、牺盟特派员,新军各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是阎锡山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召开的公开反共动员会议。事先,区党委认真研究了阎锡山召开这次会议的意图,决定派张友清同志到秋林,作为省委代表配合、协助薄一波同志,领导进步势力同阎锡山顽固势力作斗争,斗争非常激烈。阎锡山在会上公开提出取消新军政委制度,取消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同时散布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的反动口号。由于薄一波同志为首的进步力量的坚决斗争,这次会议拖延了三个月之久,无具体结果而散。但是阎锡山的反共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了。与此同时,阎锡山又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工团、突击队等组织,派到二战区专门对付共产党,搞暗杀活动。我们也针锋相对,发现敌工团,就坚决干掉。到了十月,风声越来越紧,区党委开始作预防措施,派肖杨同志到秋林,协助张友清同志做那些呆不下去,受到怀疑的党员的疏散工作。这一工作主要是通过牺盟总会的牛荫冠同志、吕调元同志,以及在阎锡山绥靖公署工作的刘岱峰同志、文化机关的赵石宾同志等进行的。整个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保存了我们党的大批力量。同时,由林枫同志亲自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研究对策。在延安,林枫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山西省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声明,经毛主席和党中央修改,在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揭露山西反动势力降日反共的企图,并号召全国人民密切注视投降派的活动。十一月阎锡山的投降反共活动准备就绪,一方面作了进攻新军的部署,一方面指使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派代表和日军代表在临汾刘村开会,要日军配合阎锡山旧军向新军进攻。当时在晋西南反阎锡山最突出的是决死二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韩钧,因此,阎锡山首先向二纵队开刀,密谋暗杀韩钧同志。同时密令他的旧军向太行山的决死一纵队、三纵队,晋西北的四纵队、工卫旅等新军作全面进攻的准备。韩钧同志由于事先得到消息,绕小道跑了回来。当时,我们正在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七大”的代表。韩钧同志回来后,既没有向区党委汇报,也没有请示区党委,就自作主张去打旧军崔道修的新一旅,把崔道修打跑了。于是,晋西南的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由于韩钧同志的错误,打乱了部署,使区党委在即将到来的反共高潮面前陷入被动。十二月初,阎锡山总部电令二纵队向同蒲线日军进攻。名之曰“冬季攻势”,其目的是要日军配合旧军夹击二纵队。韩钧同志识破了阎锡山的这一卑劣阴谋,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并向阎锡山发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电报,于是阎锡山正式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并发出讨伐“叛军”首领张文昂、韩钧的命令,发动了向新军的全面进攻,点燃了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战火,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阎锡山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主要事件,这个事件又称之为“晋西事变”。
十二月事变发生以后,区党委把正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迅速结束。立即投入了回击阎锡山反共高潮的战斗。区党委向中央发了电报,汇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中央指示:坚决回击阎锡山的进攻,但要争取阎军内部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具体作法是狠狠打击所谓“讨叛总指挥”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的部队,不公开刺激阎锡山。打仗时一律以二纵队的名义,但是在林枫同志的领导下,陈士榘、黄骅同志指挥的晋西支队以及所有新军全都参加了战斗。与此同时,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正式成立“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由二纵队政委张文昂同志任总指挥,韩钧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后方留守处,包括区党委、专署机关、报社、剧团等由我负责。指挥部成立以后,在隰县高家条村召开了誓师大会,并每天向中央军委电报战况,接受中央军委的具体指示。我们的具体打法是:由林枫和黄骅同志率领晋西支队的两个团,正面堵击敌人,轮番出击,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把阎锡山的晋绥军一直阻止在隰县以南,不让它过来。同时,由陈士榘、韩钧、刘德明等同志带领新军(约七、八个团的兵力)包抄旧军的主力,歼灭其有生力量,从旧军那里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来补充自己。但阎锡山也很狡猾,他并没有把主力放在洪赵一带,而是沿着黄河往下走。企图切断我们和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对我新军和晋西支队实行包抄。结果,这一仗没有打成。战斗继续了十多天,我们的弹药不多了,中央军委命令我们转移到中阳县靠近黄河的“下三交”一带,从陕北补充弹药。但阎锡山的旧军抢先一步,把黄河渡口抢占了。于是,中央军委又命令部队北上,穿过日军封锁线汾离公路,向晋西北转移。战斗部队好办,边打边走,我这一摊子不好办,所有各部队的后方留守处都归我照管,既要保护妇女、儿童,又要关照骡马、箱子;既要防止敌人的狂轰滥炸,又要招呼每个人不要掉队。成天翻山越岭,不停地行军。随后,区党委派钟人仿同志带领决死二纵队五团来协助我,担任后方的守卫工作。我们可高兴了,但钟人仿同志却幽默地说: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是来唱“空城计”的。原来他们连一点弹药也没有了,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部队到了汾离公路南边以后,黄骅同志经过侦察,认为离石城是敌人的大据点,其北面的大武镇日本人也比较多,西边的柳林据点日本人不多,有点伪军,决定部队绕过离石,从柳林附近过公路。入夜以后,我们用机枪封锁敌人的碉堡,掩护部队过公路。据点里的敌人以为我们要攻据点,惊惶失措,胡乱打了一阵枪,慌张地冲出来,逃到离石去了。我们安然过了汾离公路,一检查,我们的部队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根据区党委的安排,晋西南的地方干部大部分没有过来,由王达成、龚子荣同志留在那里领导地方干部坚持斗争。
我们到达晋西北临县、方山、静乐一带的时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从延安赶到了晋西北,把原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彭(绍辉)八旅、决死四纵队、暂一师(暂一师为原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支队组成的,全称为“暂编第一师”,师长为续范亭)、工卫旅和晋西南过来的部队统一起来,组成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续范亭同志任总指挥,统一行动,反击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原来的计划,只是打一下晋绥军,使其不敢再向新军进攻就可以了。没有想到晋绥军不吃打,一接火,就溃不成军,赵承绶的骑兵军也于混乱中逃过了汾离公路。晋西北成了我们的一统天下,至此,阎锡山消灭新军、困死八路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为了维护我们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党中央指示我们,新军部队不要越过汾离公路去追击晋绥军。这时,贺龙、关向应同志奉中央命令率领一二〇师又重新回到晋西北。以后,党中央派王若飞和肖劲光同志赴秋林,以二战区朱德副司令长官的代表身份调解新旧军冲突。当时和阎谈判达成的协议为:停止内战,并规定汾离公路以南是旧军的吃粮区,以北为新军的吃粮区。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我党我军的抗日反顽斗争,在晋西南地区完全转入地下,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但晋西南一直是属于晋绥边区,所以我晋绥边区的地图,从同蒲铁路线以西的绥远一直到晋南永济县境的风陵渡为止。
十 四
晋西事变以后,我的身体因疲劳过度,肺炎病复发,大口吐血,就住在方山县城疗养。方山县城,实际上是个小小的山村,我在这个山城住了大约一个月。这时,我发现吃的牛羊肉有股怪味,追问之下,始知是由于无知,竟把阎锡山所办的农牧场中荷兰牛和美利奴羊这些珍贵种畜也宰杀了。当即建议党区委制止,挽救了对于这些进口的种牛、种羊的斩尽杀绝。随后我回到了临县,后来又到了兴县。
晋西事变以后,晋西北成了党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唯一孔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抗战初期,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一二〇师从日本人的占领区中解放了七座县城,开辟和建立了晋绥根据地,党和群众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但这里和晋西南比较起来,因自然条件差,群众生活更苦一些,是山西最穷苦的高寒地区,无霜期很短。比如方山县,生长作物的时间不到一百天,农作物的品种也受到限制,很多地区多种荞麦和其他的小杂粮,如胡麻、糜黍、荞麦之类,产量也很低。沿黄河地区的离石、临县、兴县比较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北部就更差,河曲保德一带的民歌中就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的歌谣。我们初到晋西北的时候,有的地方的孩子们没有裤子穿,所谓“糠菜半年粮”,生活之苦是可以想见的。
阎锡山挑起的十二月事变,不仅未能消灭新军,反而“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把晋西北的全部旧军赶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抗日根据地,我们搞得很彻底,阎锡山的反动势力垮得也很利落。整个地区,除原来的邮局以外,所有的旧政权都垮台了,所有的旧人员,逃走了一批,关了一批,经教育后又释放了一批。整个晋西北成了我们的一统天下,磨擦、扯皮的事没有了。在根据地内部彻底摧毁了阎锡山在各地的残余势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根据地的建设,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各根据地还是不多的。在大规模的战事结束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贺龙、关向应同志主持,在临县窑头村把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成立了晋西区党委,由林枫同志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同志任副书记,王达成同志任组织部长,刘俊秀同志任民运部长,龚逢春同志任社会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一二〇师奉命从冀中回到晋西北后,原属一一五师的晋西支队开赴山东归还建制。决死二纵队、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开赴边山同蒲线一带,开展对敌斗争。同时成立了以续范亭同志为首的新军总指挥部,罗贵波同志为新军政委,雷任民、张文昂同志任副总指挥。政权建设我们抓得也很紧,二月份就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并向阎锡山发了电报,以保持在二战区内的统战关系。行政公署由续范亭同志任主任,牛荫冠、武新宇同志为副主任。参加行署领导工作的当时还有刘墉如、段云、梁鹰庸、汤平、黎化南、杜心源、张文昂、张隽轩,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刘少白、孙良臣。行政公署下设八个分区,并委任了专员以及各县县长、区长,同时,还重新调整了各地委、县委等党的领导班子。建立了晋西北军区司令部,贺龙同志任司令,关向应同志任政委,续范亭同志任副司令员,周士第同志任军区参谋长,陈漫远同志任副参谋长,甘泗淇同志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后勤部长为陈希云同志,军区卫生部长为贺彪同志。司令部开始住在兴县城附近的李家湾,后来迁到蔡家崖;区党委先住高家村,随后移住离蔡家崖不远的北坡村;行政公署原住在蔡家崖,后移住在赵家川口。至此,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设初步完成。
但是,困难也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党、政干部集中在这里,群众供应不起,部队和地方的生活非常困难。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进驻到陕甘宁边区的绥德专区,另有特殊任务。当时有许多单位,每日三餐吃黑豆,盐和棉布也很紧张。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和阎锡山打了败仗,吃了大亏之后,并不甘心。国民党政府已经调第一军李文部队进驻西安,有向陕北、晋西北进攻的趋势,我党不得不预作准备。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经贺龙、关向应晋西区党委作了认真的考虑之后,作出了开展“四大动员”的决定。“四大动员”的内容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具体说来,就是筹款,做军鞋,筹粮,参军,这四项任务都是硬梆梆的任务,不完成,我们就无法渡过困难,应付局势。但是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若不制订出明确的政策,又要脱离群众。扩军、做军鞋问题不大。筹款筹粮就颇为苦难,因为一般的群众生活水平很低,并无余粮和存款,相反的,有些赤贫户还等待政府救济,所以,不能在他们身上打主意。钱和粮都在地主和富农手里。地主老财们的粮食吃不完,就用大磁瓮装起来埋在地下。当时阎锡山的票子不值钱,群众称之为“大花脸大讨债,二花脸二讨债”。存在手里很危险,说不定哪一天贬值得一钱不值了。地主老财们就将票子换成白洋,装进坛坛里,也埋在地下。经过动员,开明一点的拿出一些粮食和款,交给政府,但是多数地主老财就是不干,有的还故意装出一副寒酸的样子,叫苦连天。但是,这欺骗不了群众。俗话说,家有千石粮,外有百杆秤,谁穷谁富,本村群众了如指掌。为此,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调查清楚以后,就发动群众挤他,施加一点压力,揭发他们剥削群众的罪恶。说服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结果动员出不少的现金和粮食,解决了很大问题。再加上区党委号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既不伤元气,又渡过难关。四大动员工作任务很快地胜利结束了。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掌握政策不严,在“四大动员”中,也产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个别地方也发生了强迫命令以及捆绑吊打地主富农,召开斗争大会的现象,但是这些错误及时纠正了,林枫同志主动承担了责任。问题是在纠偏过程中,又出现了右的偏向,有的地方把责任推到下边,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处理“四大动员”中的积极分子,甚至发展到枪毙积极分子,影响很坏。一九四〇年九月,我赴延安路过兴县康宁镇,正好碰到枪毙“四大动员”中的积极分子事件。受害人是康宁镇的一个石匠,枪毙他的理由是他拉了地主家的一头牛。当时,我出面说情也不行,还是枪毙了。我到了临县就和当时的三地委书记白坚、组织部长魏怀礼、宣传部长卫一清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立即给区党委写信,反映下面纠偏中的偏差,区党委了解到,这类现象不是一件两件,于是,很快做了部署,这种纠偏中的偏向也得到了纠正。
在“四大动员”过程中,群众团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工会的负责人是王永和同志,农会的负责人是吕韻同志,青年联合会的负责人先后是罗毅、周颐、张凡同志,妇联的负责人是姜宝箴、张育英等同志,文联的负责人是亚马同志。一九四一年,为了加强领导,区党委把各群众团体合组为“抗联”,即“抗日救国联合会”,总负责人是阎秀峰同志。在赴延安以前,我负责宣传工作,所以这里着重说说文化界的情况。
油印的《五日时事》报,到了晋西北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个时期,后来从赵承绶的骑兵军缴获了铅印机,设立了印刷厂,就改为铅印的《晋西大众报》,仍由王修同志负责。这张报纸是通俗报,是面向农民群众的,续范亭同志为这张报纸题写了报头,晋绥分局成立以后改名为“晋绥大众报”。这时赵石宾同志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区党委便决定出版区党委的机关报,取名为“抗战日报”,由赵石宾同志主编。赵去世后,廖井丹、郝德青、常芝青、周文同志先后主持报纸工作。郁文同志从新华总社来到晋西北后,就留下来负责建立新华分社,即晋绥总分社,并主持其工作,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事了。这里介绍一下赵石宾同志的情况。赵石宾,山西榆次县人,抗战前的地下党员,他是牺盟总会的最早一批工作人员,总会宣传委员会的骨干。他既能写政论文章,又能写快板鼓词,是个多面手,文字干净利落、深刻犀利,是难得的宣传干部。他一直在牺盟总会工作,后来跟随牛荫冠、吕调元同志到了秋林,任黄河出版社的总编辑,文化界地下党的负责人。十二月政变以后,他从秋林偷跑到延安,他在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工作会议之后,就到了晋西北。他从延安带来了一份毛主席的报告“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记录稿,由他整理出来并加了封面,由区党委油印科曹速同志刻印成册,发给干部学习。此后,阮迪民、高丽生、邵挺军、王雷行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也先后来到晋西北,这就大大充实了宣传、文化工作的队伍。这一批同志分别分配在“抗战日报”和“晋西大众报”工作。赵石宾同志主持“抗战日报”工作期间,非常认真,辛苦,对歪风邪气,嫉恶如仇。因积劳成疾,一直发展到咯血,医治无效,不幸在河西贺家川医院去世,实在令人痛心,这是我到延安以后的事。他逝世时才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呢!
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们也狠抓了文化教育工作的建设。大约五月间,我们在兴县召开了文化工作座谈会,号召分散在各个单位的和部队的文化工作干部归队,创建晋西北地区的各种文化机构。在这次座谈会上,贺老总、关向应、续范亭等同志都讲了话,肖三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到会的同志明确了开展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对以后的工作起了很好的影响。文联住在兴县城,再往后住在西坪村。当时,亚马从工卫旅调来当文联主任,卢梦从决死四纵队调来担任副主任,文联成为抗联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文化艺术团体,还有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这是一个当时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表演话剧的团体,负责人是欧阳山尊等同志。这个剧社不仅在晋西北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就是在晋察冀边区,在延安也有很大的影响。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都有剧团,或文化宣传队,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除“抗战日报”社、“晋西大众报”社外,还成立了“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些小丛书、剧本等。晋西北根据地,直通延安,得天独厚,所以,延安文化界有什么活动,消息很快就传到这里,我们得到很大好处。随后,在抗战七周年时,边区还举办了“七·七·七”文艺奖金会,对于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创作中的优秀作品,进行评奖,起了鼓舞创作的作用。以后继续创作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如“吕梁英雄传”。“王德锁减租”、“打得好”、“刘胡兰”等,颇受边区的部队和群众的欢迎。
我在晋西区党委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多时间,九月就到延安去了。这半年,可以说是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开始阶段,这也可以说是一场开场锣鼓。
张稼夫 述
束为 黄征整理
(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