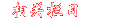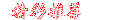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庚申忆逝(15)
发布日期:2016-02-17 17:43 来源:《庚申忆逝》 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 五
当我离开晋西北将要去延安之际,我想将一九二七年四月入党,直至一九四〇年九月的这一时期的经历再回顾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当时我的入党并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经过了实践验证后所下定的决心。中国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多次的起义都失败了。只有经过一九二三年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制订了以俄为师的三大政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后,同样的军队和同样的人民,不到一年的时间,北伐军就胜利到达武汉,收复了武汉、九江的英租界,并进而会师郑汴,全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可以成为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投靠国际帝国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加以我们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投降政策,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彻底失败。那时我还坚定地不相信中国革命会失败,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为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那样,当时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是经过一个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我们当时还顾不上读书,而且除了《共产党宣言》等少数马恩原著以外,尚未翻译出版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可读。那时我开始接触到一点列宁的著述,还是从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 A、B、C》这本小册子中所引用的列宁的论述中得知的。当我首次了解到列宁讲的“一个慎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自己所犯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我十分叹服!
“七·一五”武汉反革命政变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依然坚信革命不会失败。依然相信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会成为第二次北伐的起点。后来我在上海接不上党的关系,不得不回到晋南临汾。我的想法是晋南为反阎派势力范围,我的社会关系较多,王瀛、朱志翰等共产党人都在那里,较易接上党的关系。想不到阎锡山这时也“易帜”了,他采取了他一贯的比蒋介石更为狠毒的反革命伎俩,将山西籍的共产党人几乎一网打尽;除了杀掉的以外,大都关进了监牢和反省院。不久,对我和王亦侠也下了通缉令,从此我就过着逃难的生活,当然谈不上读书的机会了。直到一九二九年春到了上海,就业于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这时我便得以实现我渴望已久的一个愿望:研究在个体小农经济的情况下,采取农业生产合作方式,应用现代化农业技术的设想;我也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得以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环境。
当时我党中央在上海四马路办了个半公开的书局,叫“华兴书局”,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的书籍。我于这年暑假参加了无锡的农村经济调查,在整理调查材料时,尽量购买了“华兴书局”出的马列主义书刊,我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书刊。当时陈翰笙同志也支持我这样做。我将这些书籍放在那里任人传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随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提倡学习辩证法。这时我也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辩证法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和研究,然收效并不理想。对于辩证法的三原则,读来读去无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举过的那些例子,我深深感到这是不可能达到广泛应用的要求的。我自己虽有独立思考的要求和习惯,对于那时候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以及罗章龙等人的分裂主义路线,都有我自己的看法;然在当时铁的纪律的威力下,也只能够敢怒而不敢言了。一次,我们在法国公园的草坪上集会,由法南区委书记大老李主持召开各个支部联合会。会上,交大支部的乔魁贤同志交给大老李一本托派刊物《我们的话》,说是在图书馆发现的。这本是件好事,反映了我们的同志对托派刊物是有一定的警觉性的。但大老李却追问说:你看了没有?乔说:我看了。于是,大老李抓住这一点就大批乔魁贤,一再上纲上线。我看不下去,说了一句他不看又怎么知道是托派的刊物呢?结果,大老李勃然大怒,说你张稼夫居然给他辩护,我宣布,给你当众警告处分。这是我入党后受到的第一次处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的情况以及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上不成熟的表现。由于我参加过无锡、清苑农村调查,又经过长期的地下党的生活,还当了两年村长,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的。我深感这些“左”的路线,不管是国际路线也罢,放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圆凿方枘,牛头不对马嘴的。但我无能为力,只好经常用“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句话来聊以自慰。其实,这也是唯心主义的话,我的这种心理状况,正好说明我的马列主义还是没有读通。
当我先后陆续读到毛主席的论著以后,这才使我对于哲学和社会科学及其有关的某些具体问题,开始有点豁然开朗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辩证唯物论”,我自己并未亲自听讲,经抗大回来的同志向我陈述了毛主席所讲的内容,和他所列举的许多;通俗而生动的事例,同时我也看到了他们带回来的油印的“讲授提纲”(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我认为经他这么一讲就真正把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变活了,如果你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话,那你也就可以应用自如了。当然我的老师很多,如刘少奇同志和杨尚昆同志、罗荣桓同志、林枫同志、张友清同志、黄骅同志等,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以身作则,对于我的具体指导,都使我逐渐得到提高,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1945年张稼夫(左)和林枫(右)在晋绥分局。
由于直接的工作关系,林枫同志对我的帮助最大。他了解我的长处,也了解我的个性和缺点。少奇同志曾说过“林枫同志会办事”,在我和他的接触中深深有所体会。他先后在省委和北方局工作时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突出的组织才能。他善于运用委婉的语气和方式,既批评人,还使你并不反感。例如当我从运城扩兵回来在刘村汇报工作时,我就没有多考虑,指责了部队某些同志的错误作法,后来听说那个同志因此受了处分,我才感到有些小题大做了。就在这时,林枫同志对我说:“少奇同志说过,稼夫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有点不会办事。”我开始还有点摸不着头脑,旋即领会到正是击中了我的要害。话虽不多,但对我的启发却是很大的。林枫风同志的会办事的事例,就充分表现在这些地方,当他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时,就已经理解了我党在独立自主原则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在少奇同志的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因而才得到了少奇同志的那句“好评”。他是那样不露锋芒、埋头苦干、平易易近人地善于接触各种同志和各族各界的友好人士。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有缺点的同志和朋友,也都能够做到取长补短、知人善任。这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值得我很好学习的。他经常对我说:“你偏激,你有善善恶恶之念”。他总是话不多,但发人深醒。我领会到他的意思:“善善恶恶”这句旧时代的格言,是小农经济环境中独善其身思想的产物。无产阶级政治家则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因为社会,总是两头小、中间大的,中间层的人也有种种的缺点毛病,如果对这些“恶”,采取厌恶弃绝的态度,就不能争取到大多数,革命就无法胜利。问题是要帮助那些有缺点的人提高进步,同臻于善,这才能团结起广大的队伍,壮大革命力量。这些道理我也会讲,但不是经常能够做到的。我也不是一个不能容人的人,可是常常由于激动的情况下,就不免要将心中容忍已久、不应该讲出的话脱口而出。这是不是就是刘少奇同志所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一个共产党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所组成的先进政党的成员,理应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度,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出发,不利于党的利益的话不说,不利于党的利益的事不做,而不应该是一个随感而发的自由主义者。这些道理我都懂得,也会给别人讲述,就是有时自己不能完全做到,这就是一个政治修养的问题了。林枫同志经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海量,他所指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具有的政治修养,这是我们应该时时服膺的箴言。
一九三八年春夏之交,林枫同志随同杨尚昆同志来到一一五师驻地孝义,一一五师师部驻在碾头村,政治部驻在申家庄,北方局就驻在张家庄。林枫同志对于罗荣桓同志和陈光同志(那时陈为一一五师代师长)尊如师长,所有一切党的重大政策问题,事先都要向杨、罗陈请示,他们相处得是那么协调一致,我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五师政治部有杨忠同志(已故)、杨勇同志、肖华同志、肖向荣同志、潘振武同志等,他们遵照毛主席的“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教导,在孝义、汾阳、灵石、汾西以及洪赵一,都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建党工作。为我们在晋西事变中能够顺利应付阎顽军的突然袭击,准备了充分的群众条件和社会基础。一九三九年春一一五师奉命进到 山东,给晋西南留下一个独立的补充团,后又扩建一个团,称为晋西支队,和区党委一起行动。支队长是陈士榘同志,副支队长是黄骅同志,一一团团长为杨尚儒同志,二团团长为何以祥同志。在晋西事变的战斗中,真正具有战斗经验的主力,就是这两个团,决死二纵队等新军的数量多、政治质量也强,然战斗经验则甚差。高家条誓师以后,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密切联系,他和陈、黄、韩等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我和张文昂是留守后方的。我军突过汾离公路封锁线,到达晋西北以后,我就病倒在方山县城。至于当时如何和晋西北区党委取得联系,如何在军三委总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的领导下,制定围攻赵承绥骑兵军的作战计划,以及关于两个区党委的合并,晋西北行政公署的成立等等,我一概均未能参加。当我回到临县时,贺、关率领一二〇师主力,已经返回到晋西北地区了,所有随后的一切组织领导工作全部是由林枫同志会同贺、关和晋西北的其他同志们共同进行的。就我所知,林枫同志对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是非常尊重的。至于林枫同志对工作中所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历来都是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和下级,这是尽人皆知的。
也许是由于他在天津南开上学时,打下了较深厚的文化基础的缘故,他是那么重视并热爱文化教育工作;自己手不释卷,同时也积极鼓励同志们学习。当晋西区党委搬到兴县北坡村时,就立即成立了党校,由他本人兼校长,将原八地委书记饶斌同志调来任党校的副书记。由于当时王达成同志尚在晋西南未归,于是就将原三地委书记宋英同志调来区党委担任组织部长。饶斌同志是上医学生,宋英同志是北大地质系学生,于是就流传有林枫重用知识分子之说。与此同时,也在兴县城内设立了“晋西师范”,由杜若牧同志筹办;在临县设立了“一中”,由王静野同志筹办。在关向应同志的倡议下,在离石县筹办了“贺昌中学”;顾永田同志壮烈牺牲后,在八分区边山筹办了“永田中学”。为了广泛地轮训“群众工作干部”,由林枫同志倡议,还在区党委驻地附近设立了“实验学校”,实际是一种类似“抗大”的中学,以学习党的政策为主,同时也学习文化知识。实验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就是由抗联主任阎秀峰同志担任的,随后郑林同志和郝德青同志都先后担任过这个学校的校长。足见林枫同志对该校的重视,而该校也确实为这一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干部。在可能条件下,各地也先后恢复了小学教育,而“冬学”则又是所有农村中都必须举办的普及性的通俗义务教育。
总之,林枫同志这个榜样对我的熏陶和教益是十分巨大的。他自己所常说的,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海量,这也就是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为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作为决定自己的言行的根据。这个对共产党的党性锻炼的要求,我认为是毫无疑义的,理应做到的起码标准。林枫同志用自己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他是能够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地完全做到这个标准。而我自己至今尚往往达不到这个标准,也只能努力勉励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这一点上我就远不如龚逢春同志,所以当林枫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特地将龚逢春同志调来做他的助手,在任劳任怨这一点上,是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
最后,我拟引用我与林枫同志之间的一段故事,用以结束我的这一回顾。这段故事的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大概是一九六〇年以后的事。那时我在文办工作,林枫同志已患了心绞痛,在家中休养,由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任文办的代主任。这一时期,我们遇到的违反党的正常生活的事例逐渐增多起来。中央文教小组的组长是陆定一部长,副组长是康生,文教小组和文办是直接有关的。由于康从中作祟,这期间不正常的事例不知有多少,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使人莫知所措。在那种情况下,连我这个容易激动的人也小心谨慎起来。于是我就去林枫同志家中,将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全部向他讲了出来,企望他能得便向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反映一下。他总是笑眯眯地倾听着我的诉说,虽然有时神情上似乎也同情我的话,却不肯明白表态。有一次,他听了以后,竟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人呀,最好退休了算了”。这就表明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就很不高兴地告辞而去。过了几天,他打电话叫我去,谈了一阵不相干的事,最后拿出一个信封来,交给我说:“这是我从《续资治通鉴》上抄下来的,你带了回去再看吧”。我回到家中,打开一看,他在一张信纸上抄了这么一段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君子岂不知?以大度容之,则庶事俱济。”据说这是吕蒙正向宋太宗讲的话。他的这一友谊的赠礼,对我说来是一种安慰,也是一个值得铭记的“箴言”。于是我就把它写在一把折扇上作为我的座右铭。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样一位宽厚厚忠诚的共产党人,也被反革命分子林彪、四人帮的军师康生、陈伯达迫害致死了。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林枫同志这一马列主义政治家的风度和党性修养的正确性。他将永远是我们当代的和下一代的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
张稼夫 述
束为 黄征整理
(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