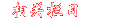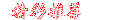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庚申忆逝(18-20)
发布日期:2016-02-18 15:21 来源:《庚申忆逝》 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 八
一九四四年底召开的边区四届群英大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敌斗争、生产斗争,减租减息运动搞得生气勃勃,部队、干部以及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群众情绪稳定,工商业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大力开展“挤敌人”的斗争,日军处于守势,已不可能频繁的进入边区“扫荡”。一九四四年秋冬,林枫、吕正操等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去了,我是副书记,虽然也是“七大”代表,为照顾工作,留在前方代理书记的工作,没有参加“七大”。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希特勒战败;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和日军早有勾结的阎锡山,命令他的部队立即进入太原等城市,日阎合流,妄图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同时也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进攻。我们党为了捍卫全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进攻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时,国内主要矛盾便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林枫同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被调到东北。李井泉同志接任晋绥分局书记,我仍任副书记。这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贺龙同志带领部队返回晋绥,一度解放文水,之后,亲自到大同前线,指挥对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作战。
这时,为了加强吕梁地区党的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了吕梁区党委。吕梁区党委下设汾西地区的九地委、新绛地区的十地委、运城地区的十一地委。张宗逊同志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罗贵波同志为副书记、副政委。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张宗逊同志调离吕梁区党委,罗贵波同志接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彭绍辉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十一月,王震同志带领二纵队到吕梁地区,改由王震同志担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罗贵波同志仍为副书记、副政委,彭绍辉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间,王震同志奉中央命令到陕北宜川一带作战。罗贵波同志又成了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彭绍辉同志仍任军区司令员,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吕梁区党委撤销为止。
一九四六年夏,中央下达了《五四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分局于六月召开了高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就关于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根据《五四指示》精神,作了比较认真的讨论。那时对晋绥地区的工作估计以及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同时对于领导作风中的官僚主义作了检查,是有收获的。但是会议中由于对过去工作片面地强调了找缺点,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例如,在各地、县负责干部汇报工作时,只准说缺点错误,不准说成绩,缺点错误越多越好,一直发展到查算一九四〇年“四大动员”时的老帐,越算越泄气,而领导却说什么“成绩不说丢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这种专看缺点的作法,到四七年初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又有了发展,指名道姓的指责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把边区工作形容得漆黑一团。后来这种做法未加制止,并进而发展为逼、供、信,于是在干部中就出现了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反正我有两个口袋,一边装的是羊毛,一边装的是猪毛,你要猪毛有猪毛,要羊毛有羊毛!”当时也竟将这样得来的材料写成文件大量散发,同时也报送给党中央。这种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土地改革中发展到顶点,在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严历批评以后,才有所收敛、改正。我自己身为分局的副书记,明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然而总以为自己参与了过去的领导不便为之辩解,未料到这样竟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自己对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惨痛教训,是我终身耿耿于怀,永远不能忘怀的!
在高于会议以后,分局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狠抓了新解放区的除奸反霸运动,同时抓了以下三项工作,这三项工作也就是把减租减息转变为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很有成效的。
第一项工作是派出工作组,作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情况的调查。工作组出发前分局在蔡家崖召开会议,布置调查任务,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先后讲了话。后来,这些调查组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同根据地初建时的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新中农普遍增多,李井泉同志强调要团结中农。由于形势的发展,这项工作尚未结束,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开始了
第二项工作是分局制订了一个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文件:“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制订这样一个文件是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井结合了晋绥解放区的农村实际情况制订的。这个文件不仅考虑到山西农村和南方农村情况有所不同,也考虑到本解放区抗日战争以来政治、经济、阶级情况的变化。负责起草这个文件的是段云、梁膺庸、吕韻、丛一平、方正之等同志。这个文件中,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并且引用本区的实例加以说明。例如:地主和经营地主,什么情况才可划为地主或经营地主,土地占有、剥削的方式和数量,然后举几个例子分别加以说明。这就大大便于农村工作干部掌握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利于即将到来的土地改运动。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曾把这个文件称为马列主义的文件。可惜的是,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开始不久,就被康生否定,全部收回烧掉了。
第三项工作是培训干部。从减租减息,过渡到土地改革,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农村政策。土地改革是一场从经济上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运动,是在农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性运动。为了适应这一运动的到来,分局决定培训农村工作干部,帮助广大干部实现思想上的转变,开办培训班,并立即把边区实验学校迁到岚县的东村,分局决定由我任校长,王文达同志任副校长。分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亲自讲课,主要是讲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政策、方针、步骤、纪律等。并联系边区农村的实际,提出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具体要求。当时,我们把农村分为四类:一类是好的模范村,村干部好,工作能力强;二类是基本上是好的,但有缺点,甚至错误;三类工作不好,领导班子有明显的问题的;四类是问题严重,不可依靠的。这四类村子,第一类和第四类是少数,总的说来是两头小中间大,这种分析大致符合实际,而且分类指导这种作法,也是比较好的。遗憾的感的是,运动一起来,由于康生、陈伯达的干扰和破坏,就来了个大放手,不加区别,几乎全部否定了基层的领导,大大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极性,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严肃批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四六年底四七年初,分局从各机关单位、部队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陆续到达农村,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
十 九
一九四七年春天,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发动了全边区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分期分批进行。“五·四指示”以后下到农村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分别编入各地的土改工作团。分局要求各工作团,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并以分局正式通过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文件为依据,划分阶级成份。运动初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很快的便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偏差,为这一伟大的运动造成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大约是在春初,康生由陕北来到晋西,到临县的郝家坡蹲点搞土改。分局派我也到郝家坡,公开说是协助康生工作,实则是所谓的“带上”。“带上”二字是康生的发明,他来到晋绥以后,对于当地的干部分为三类,采取三种办法。第一类是好的,叫做“依靠”;第二类是差的,叫做“带上”;第三类是坏的,叫做“超过”。看来,我是被划为二类,“带上”了。从此以后,整个土改运动,我只能在郝家坡被康生“带上”,对于全区的工作,分局的工作,完全脱离。分局的会议不能参加,文件也不能及时看到,我这个分局的副书记,名义尚在,实际上无形中免掉了。所以,对于分局如何领导这一运动的,我并不了解。在土改运动中,有一次,王震同志曾经问我:“你怎么把小学都取消了?”我说:“我怎么知道呢?我在郝家坡,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不清楚。”只是对郝家坡的情况和康生的情况,以及一些比较明显的现象,记忆犹新,写了出来,只能算作一得之见吧。
土地改革运动,是在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背景下发动的,这一运动对于解放战争,总的说来起到了突出的支援作用。其次晋绥的土改却又是在我党从上到下全面掌握领导权已达七年之久的情况下进行的。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蜕化变质或是被地主富农篡夺了领导权的是极少数。土地改革运动应当主要地依靠这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而不应一脚踢开。再其次,以“四大动员”起到土改的七年中,农村出现了一些新中农,这批新中农原来是贫农,由于我党的阶级政策的实施,他们才得以上升为新中农,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应当和其他贫农一样,是依靠的力量。至于土改的主要对象地主,情况也有某些变化。有一部分地主、富农的土地数量远远超过平均数,还在依靠出租土地和高利贷剥削农民,还有相当的资财。但是,同样也应当看到,“四大动员”、“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公粮条例”以及其它税收和负担的政策的实施,相当一部分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资财已经不多了。例如,晋绥边区的第一流的地主牛友兰,已经下降到免征公粮户。“四大动员”时,他捐献资财很多,也很主动,被称为开明士绅,所以他被推举为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一二〇师的司令部就设在他的院子里。他在河西办了个纺织工厂,也全部捐献给边区政府,他老婆死的时候,边区政府还送了花圈。可是,在土改中,牛友兰成了主要斗争对象,死得很惨。康生所在的郝家坡有个地主叫刘佑铭,一九三六年初,红军东渡时,被打了土豪;四大动员,减租减息,以及各项负担,他都是重要对象;到土改的时候,已经破产,地卖光了,老婆孩子没有了,一个人住在一眼破窑洞里。我向康生反映这个人的情况,他说这是“化形地主”。他的地是卖光的,不是分配的,不能算作土地革命,没有土地。应当挖他的浮财和底财。影响更大的是陈伯达参加的兴县后木栏干村的土地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写了一个“后木栏干调查报告”,分局把它铅印成册,发到各土改工作团。这份报告提出要查三代。据说,在后木栏干搞调查的一个负责干部,跑到野外墓地,查看墓碑,以此为依据划成份。这么一查,好些党员、干部、民兵的成份,虽然早已下降为贫农,或者本来就是中农,土改中却被当成地主,挨了斗争。同时在“后木栏干调查报告”中,除了强调了查三代这一条以外,还强调了“看铺摊摊”和“看政治态度”两条,这样就将土改的打击面扩大化到异常严重的程度了。后木栏干村在划成份前只有两户地主,占总户数五十二户的不到百分之四,划成份后把剥削阶级划成二十一户,占到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寨县东秀庄行政村在土改复查中,发动群众审查和改订阶级成份,由过去地主一户改订成十九户,富农二户改订成十户,中农七十五户改订成三十六户,贫农三十五户改订成四十四户,其他一户改为五户。地富的比例由原来的百分之三上升为百分之二十五。(详见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晋绥日报》头版消息报道:《五寨东秀庄土地复查中发动群众,审查改订成份,清查出大批地主,群众觉悟提高》)不少地方,甚至把工商业者当作“化形地主”,公开侵犯他们的利益。康生在郝家坡常说:“地主是老财,老财就是地主”。对工商业者,康生有句定义,即“无商不奸”。对待干部同样以感情代替政策,把那些些了解下情的基层干部(他们知道地富土地已经分散,搞不到多少斗争果实)的说法一概视为“右倾”和当作土改障碍而“超过”,叫做“搬石头”。郝家坡支部书记名叫严朝臣,贫农成份,作风正派廉洁,就是有点好人主义味道,胆小怕事。康生认为这种人不能用,不能依靠,一直发展到把支部也一脚踢开。在这里,可以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兴县胡家沟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审查党员”错误的口号影响下,批判了二区区委组织部长刘初生,称他为“候补敌人”,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实际上,刘初生是个有影响的较好的干部,兴县的许多干部得知刘初生被斗、被撤职的消息以后,反映非常强烈。认为象这样的好干部被打成“候补敌人”,咱就早该撤职了。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当时,我虽然是被“带上”干工作的,对这些不符合党的,的政策的作法,看不下去,常和他争论,因为我是被“带上”的,没有发言权,最终还是康生说了算。在郝家坡搞土改工作的还有李伯钊、杨之华、谷羽、毛岸英、魏怀礼,以及太岳区派来的郑海等同志,他们都认为康生的做法不恰当,也给他提了意见,但是康生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一概斥之为右倾。也很霸道,他说的话,还要我们作记录,油印出来存档。这些东西很多,可以在中央档案局查到。
“左”的错误越发展越严重,康生看了“后木栏干调查报告”,认为很好;可是对分局制订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却大发议论,说是这个小册子在重庆可以用,在晋绥不能用;并且说当我军打过了长江时,就要宣布“土地国有”了。不久,分局下通知把这个文件统统收回来,烧掉了。毛主席一九四八年路过晋绥时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毛主席说的“那么一点”指的就是那本“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正确的政策不要了,只好听康生、陈伯达瞎指挥。当时,郝家坡附近出现了打人的情况,不仅打地主、富农、也打干部、党员。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他不仅不制止,反而说什么,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义愤嘛,打几下也可以嘛。不久,打人之风便盛行起来,捆绑吊打一齐上,伤害了许多干部党员和中农,也打死一些好党员、好干部和积极分子,著名民主人士孙良臣也被打死,在群众中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一九四七年初夏,康生在郝家坡召开土改经验交流会,各地土改代表团都派人参加。正在静乐县领导土改的陈伯达也来了。陈伯达去静乐县搞土改比我们郝家坡晚一些,但他很快就搞完了。陈伯达在会上发言,介绍他在静乐县搞土改的经验,题目是“遇事和群众商量”,实际上就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甘当群众的尾巴。晋绥分局通过的以农会名义公开发表的“告农民书”就号召什么“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公然宣扬不要党的领导,这一套尾巴主义的东西确实是从康生、陈伯达那里弄来的。在运动中,陈伯达在静乐县枪毙了一个民兵英雄,说是恶霸,是“狗熊”。接着,他又抓了一个“五虎弟兄”,晋绥日报又加以宣传,这可就不得了了,这里也有“劳动狗熊”,那里也有“五虎弟兄”,闹的不可收拾。在这个经验交流会上,康生大谈其挖底财的经验(实际没有挖出多少),陈伯达听了大叫起来:“唉呀,我犯了个大错者误,忘了挖底财啦,我要补课!”。本来,他在静乐县搞的那个点的土改结束了,却又匆匆赶回静乐县去挖底财,“左”的劲头真可以呢!
对于康生、陈伯达的那些作法,晋绥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早就有抵触情绪,非常反感,康生不仅不作自我批评,反而大骂晋绥干部思想右倾,跟不上形势,要继续“搬石头”、“贫农团要代替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打乱平分”。在此种左倾思想基础上,《晋绥日报》发表了内容非常错误的“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还发表了针对工商业者和地下工作者的评论“过河必须拆桥”,这种言论不仅错误,而且造成的后果十分恶劣。报纸上还发表了批斗晋西北临参会副议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的的长篇消息。影响所及,又是火上加油。一九四七年七月,晋绥分局召开土改整党工作会议,又称之为地书会议,各地委书记,土改工作团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是按照康生、陈伯达的旨意召开的。当时,本来运动已经搞得很“左”了,但会议的主题却是继续反右。通过这次会议,土改中的那一套“左”的东西合法化、系统化了。林枫同志是缺席受批判,而我是被作为批判对象参加这次会议的。会后不久,我就率领晋绥代表团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由党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上,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这个、大纲中,提出了成立“人民法庭”处理罪犯的规定。我们回来以后,在分局机关干部会上作了传达。但是,分局未提出任何具体措施,以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而是任其发展。
一九四七年底,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在会前,毛主席派乔木同志来临县调查划分阶级成份扩大化和侵犯私人工商业的错误。同时,乔木带来毛主席在苏区划分成份的小册子。其中规定地、富成份不能超过百分之八,而当时临县几个点都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明显地把一些中农划到阶级敌人阵营中去了。中央的这次会议批评了晋绥在土改中的错误。李井泉同志参加了这次中央会议,回来以后,及时发了三个关于纠正“左”的偏向的指示,但有关中央这次会议的情况,就连我和龚逢春同志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主席路过晋绥和我谈话时,才了解到在中央会议上批评晋绥分局的情况。四月一日毛主席在蔡家崖军区礼堂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于晋绥边区的工作以及土改的成绩作了充分的全面的估价。毛泽东同志指出:“晋绥的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这表现在实行了减租减息,相当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纺织业、军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建立了党的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万人的人民军队,因而就能依据这些工作基础,进行了胜利的抗日战争,并打退了阎锡山等反动派的进攻。当然,这个时期的党和政府是有缺点,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成份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工作上的不良现象。但是,就总的情形来说,抗日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估价,完全符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深受晋绥广大党员的拥护。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晋绥的党组织在工作中发生的“左”的偏向,主要地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改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过去一年中,晋绥在这方面曾经发生的偏向,现在也已纠正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三〇五页)毛主席的讲话,成了晋绥土改后期工作的指路明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偏向。例如:末期土改尚未分配土地的地方,把打乱平分改为抽肥补瘦,填平补齐。又如,对部分错误地被开除的党员恢复了党籍,对部分受到侵犯的中农的财产也得到补偿等,受到群众的拥护。
会后,毛主席应邀亲笔题写了两张条幅:
一张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
一张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毛主席的这两条题字,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后来,全国各地都影印了这两张条幅,供干部认真学习,指引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 十
一九四八年春,在我党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在粉碎了胡宗南向陕北的进攻的同时,将我人民解放军组成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经过冬季的新式整军以后,有计划地分工配合,向敌人发起了春季攻势。四、五月间,由王震同志领导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先后解放了晋西南地区的阎顽在隰县和运城的两个坚固据点。与此同时,由陈赓同志的部队负责对阎顽的临汾据点的进攻。阎顽虽擅长于守城,我军采取了爆破战术,临汾城也指日可下。在临汾城尚未攻下之前,我党中央为了支援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任务,决定将解放了的晋南地区划归陕甘宁晋绥,作为向西北、西南地区进军的战略后方。于是当即成立了晋南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派出机关,书记是武新宇同志,副书记是龚子荣同志。临汾城解放以后,中央又决定委派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马明方同志兼任晋南工委书记,武新宇、龚子荣任任副书记。我自己当毛主席路过晋绥边区时,曾经多次要求到基层搞实际工作,因此,经主席同意,派我任晋南工委副书记兼临汾县委书记。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中央和晋绥中央分局,接受了我多次请求,给我一个到实际工作中锻炼的好机会;同时,我也感到遗憾,这遗憾不是由于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这只是个人的区区小事,不足介意;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眼看着工作受到损失,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就离开了老区的群众,心中实在感到惭愧。那么,我只有一办法,也就是接受经验教训的办法,把新解放区的工作搞好,以驱散淤积于自己心头的内疚情绪。
当时,临汾县委的主要工作是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们的理论、政策武器就是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还有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那时,临汾县委的副书记为冯克心同志,临汾县长为张平同志。在工作中,我们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临汾县的河西地区,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我主要是依靠了慕生忠、魏怀礼、彭德、赵守攻等同志。慕生忠同志是陕北老干部,我把汾河以西以北的一摊子交给他,所用的大多数是分局党校中在土改期间被打下来的干部。魏怀礼也是陕北老干部,在瓦窑堡挖过炭,抗战初期,是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开辟人之一,当时任吕梁区党委组织部长,由他来主管临汾以南、金殿一带。彭德当时是晋南十地委的党委书记。赵守攻是十地委委员兼新绛县委书记,领导本地区的土改工作。晋南地区的土改工作比较稳,进展也比较快,没有出什么大的偏差问题。一九四八年底,晋绥分局通知我和武新宇同志回去开会(此时我仍是中央分局的副书记)。我到兴县时,才知道是要召开党代表会议,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事先我也毫不了解。当时,李井泉同志去了绥远,没有参加会议。到开会时我才知道开会是要统一思想。那么统一什么思想呢?原来,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分局受康生、陈伯达左倾错误的影响,在运动中伤害了不少群众和干部,中央,特别是毛主席指出晋绥土改中的错误以后,纠偏工作搞了一些,但是很不得力,落实政策的工作也不够好,因此,有些干部对晋绥分局的意见很多。我猜想,分局召开这次会议,大概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总结经验,促进团结。我想要达到这个要求,如果参加会议的某些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曾经出谋献策、推波助澜、胡编乱诌的人,也都作点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担一些责任,情况就会好得多。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大有想把土改错误的责任全部都推到少数领导同志身上的企图。显然这种做法是恶劣的和不公平的。结果,只是由张子意同志代表分局做了工作总结,笼笼统统检讨了几句,一参加会议的同志很不满意。我仔细观察了一番,分局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意思,而我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后来,主席团的同志一再要我讲话,我就说,中央已经下达了文件,当前主要是把今后的工作搞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会议草草结束。我记得西北局的马明方同志和贾拓夫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党代表会议。年底我回到晋南去,没有工作多久,中央就调我去西北局工作,匆匆离开临汾,到了延安,这已是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了。
调我到西北局,是去接替李卓然同志的工作。李卓然同志是西北局宣传部长,因为东北局的何凯丰同志调中央去了,中央就调李卓然同志去东北,我就被调到西北局。西北局的书记是彭德怀同志,副书记是习仲勋同志和马明方同志,马文瑞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这时贺总、王维舟、张经武等同志都和我开玩笑地说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等等。我说我是安泰,刚刚匍伏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现在又悬到空中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会被阶级敌人扼死的。我到延安只有两个多月,西安就解放了。六月初,西北局迁到西安。从延安到西安,工作对象、任务不同,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当地主要工作是接管、剿匪、反霸、统一战线,有的地方搞土改。我们的武器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工作忙得很。文化、教育、卫生、民主人士、民族问题,头绪很多,以后搞了城市的三反五反和农村的土改运动。我还随同习仲勋等同志到新疆解决民族工作中的问题,南疆北疆转了个大圈子,接着还搞了西北地区文教系统的三反五反运动,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底,我才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这一段工作,身体比较疲乏;还患过病,但工作顺利,心情愉快,最大的收获则是西北局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北局的书记彭老总对干部很信任,很放手,除了制订本地区的大政方针,工作计划和检查工作外,他主要抓了西北第一野战军的工作。而第一野战军的总部是设在兰州的,同时他也常到各地指挥解放大西北的战争,西北局的日常工作由习仲勋同志主持。整个西北局的领导工作很放手,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下面的干部也不都很强,不是个个是天才,但是工作得很好。彭老总、习仲勋同志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制定方针政策,干部人人心中有数。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的任务,一是出主意,一是用于部,要做到知人善任,彭总和习仲勋同志可以说是深得要领的。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党内生活非常健全、民主。那时,西北局常委定期开会,我是常委之一,每次会议都提前将会议讨论内容印发给常委每人一份,以便早作准备。大自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小到人事任免名单,都是集体讨论决定。不搞一言堂,不搞突然袭击,而是作到认真、稳妥、人人心情愉快。例如毛主席曾对西北地区的工作有过多次指示,大意是讲“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民族问题复杂,你们要搞得稳些,不要性急,不要抢先,搞少数民族工作,要先把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搞好,不然就很难接近群众,这是我们搞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长征时你不和上层人士搞好关系,就很难接触群众,群众也不敢接近你,千夫长,百夫长,一声令下就把你干掉了。陕甘宁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一定要把民族问题解决好。”西北局常委会对毛主席这些指示,进行过认真的传达和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我记得,甘肃省甘南地区(现划归青海省黄南地区)有个名叫项前的部落千夫长,由于不了解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动不动就造反,拒绝我们进入他们那个地区。我们就耐心地做工作,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搞到七、八次,终于得到他们的信任,打开了局面。对于民主人士,凡是过去和我们合作过,为人民作过一些好事的,都予以适当照顾,安排了工作,,而不是过河拆桥。李鼎铭、邓宝珊、高桂滋等等都按排了工作。后来,有人说什么西北局的工作右了,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是单用左眼看问题的论调。
我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彭老总、习仲勋同志领导有方,任务那么重,头绪那么多,但是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领导很注意团结,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有问题就摆在桌面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没有团团伙伙那类不正之风。我初到西北局时,耽心人生地疏,不好工作,不久,这种耽心就消失了。彭老总、习仲勋同志鼓励我放手大胆工作,同志们处得也很融洽。彭老总比较严肃、内向,但从来不板起脸孔训人,他对人是非常赤诚的。习仲勋同志的担子最重,但他善于发挥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上支持、信任、帮助、提高,还关心干部的生活。所以,他很主动,每天晚饭后,约我们到城墙上散步,潇洒的很。
西北局的民主、团结、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可见印象之深。
张稼夫 述
束为 黄征整理
(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