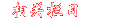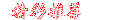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一)(05月09日)
- 贺大姐和红军后代到卢氏(05月08日)
- 军刀的故事(05月06日)
- 一位海军将军的期盼……(04月23日)
- 祭奠归来随想!(04月18日)
庚申忆逝(21-22)
发布日期:2016-02-18 17:03 来源:《庚申忆逝》 作者:晋绥基金会
二十一
一九五二年底,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西北局,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科学院是建国初期成立的国家最高学府,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有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等科学家,还有陈伯达。我到科学院以前,科学院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恽子强同志,副书记是丁瓒,中央调我去科学院,任命我为副院长,党组书记,恽子强分工管数理化方面工作,丁瓒调心理研究所。我到职以后,习仲勋同志和胡乔本同志(当时习仲勋同志任中宣部长兼中央文委副主任,乔木同志任中宣部副部长,于光远同志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我多做调查研究,搞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把科学院整顿一下。
为了便于以后的工作,又让我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学习他们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代表团团长是钱三强同志,秘书长是武衡同志,给我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代表团的成员选的都是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其中党员有刘大年、沈其震、刘咸一、曹言行、宋应、张勃川、汪志华、康瑛、何祚庥等人。这次访苏的任务是:(一)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三)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方针是以学习为主,以团结为重,客随主便。当时,通过朝鲜战争,中苏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中央嘱咐要慎重对待两国关系。
代表团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下旬动身的,三月五日到达莫斯科。我们到达离莫斯科还有三站的地方,忽然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来了解到,斯大林在逝世前,对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访问,已经作了指示,要苏联科学院热情接待,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如对历史分期问题,不要争论等等。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秘书长托普切也夫以及要参加各种吊唁也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活动。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理、工、农、医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专家,还有行政组织干部,要求不一,参观访问也就分散对口进行活动。我自己的任务是着重于了解联共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和情况,更多的是和科学院党的领导以及基层支部、小组座谈。我们了解到,苏联科学院有八个学部,分得很细。学部是学术行政领导机构,许多科学家到车站迎接。但代表团几乎成了奔丧团,活动,守灵,参加追悼会。在参加吊唁活动的同时,科学家通过学部进行活动。联共党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科学院学术秘书处进行的。学术秘书处由十几个科学家组成,都是党员,在学术上是博士以上的专家。学术秘书处实际上是联共党领导科学的中介,通过这个秘书处把联共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同时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来。主席团会议讨论的问题、计划、措施等,都由学术秘书处首先提出,经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施。当时苏联科学院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状况,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无隙可击的科学战线”,而提出的工作方针则是“全面安排,重点使用力量”。他们这一套组织很科学,工作方法很灵活,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在座谈中,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他们还列举了若干列宁对待知识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许多科学家跑到外国去了,共党就尽量争取团结留在国内的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优越条件。如著名生理学家、条件反射论的创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联共党的反对派,科学院一连给他派了六个党员做助手,他坚决不要党代表,都被他撵了出来。列宁指示对巴甫洛夫还是要尊重,认真做团结工作。巴甫洛夫创立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的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列宁对待高尔基的态度也是人所共知的。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对苏联科学院因陋就简的精神印象很深。科学院院部就设在清朝李鸿章当年在俄国办外交的楼房里;好多科研人员没有限公室,写字台放在走廊里,非常俭朴,工作效率却很高。
苏联科学家对我们很友好,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很关心,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中国的农业有很大的优越性,有几千年历史,认真地总结瓦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应用,可以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
尽管苏联对我们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单位就不让我们参观,有个很小的原子能研究所,也只让钱三强等少数几个人看了看,说是国防系统,要保密。在莫斯科的访问结束后,我们到列宁格勒,参观当地的入学、科研机构,以及有关的十月革命遗迹和纪念馆,参观结束
后回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随后又乘专列到基辅、乌兹别克,取道西伯利亚铁道,参观了伊尔库次克和西伯利亚科学分院,然后回国。
我们在苏联参观访问三个多月,于五月底回到东北。为了综合各学科的参观记录,在长春小住,由刘大年同志和汪志华同志起草给中央的“访苏报告”,最后由武衡同志修改定稿,上报中央。在这期间,我们还顺便对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科研人员只许看俄文书刊,其他外文科技书刊都锁了起来,理由是其中有西方骂斯大林的文章,不准看,来了个因噎废食。我们到苏联参观,人家首先让我们看图书馆,藏书多少,备有多少外文书籍期刊。书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东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来的。因此,苏联科学部门把这看成是科学水平的标志之一,而不搞闭关自守。我们才开始搞科学,经验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向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学习,不看外国的科技书刊怎么能行呢?后来又了解到,全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和扩大了情报研究所和图书馆,并且规定各种外文资料邮来以后,要求在一周内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这一启发的结果。二是科研机构不宜轻易搬动。我在长春时,物理化学所和仪器馆的负责人向我诉苦,这两个机构都是从上海搬来的,原来的基础很好,长春的条件也不错,搬一次家,折腾了三年都恢复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当时,刮起一股搬迁风,外地的科研单位都想搬来北京。于是我们便作了一条规定,原有科学单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刹住了这股歪风。后来,科学院在兰州建立分院,吸取了东北的经验,就是先抓建设,盖房子,安装机器和水、电、煤气,等一切科研工作条件都就绪了以后,再从北京、上海等地调人来,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于搬迁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是张德生同志,他对我们建院工作很支持,我们还请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第一任的院长。
“访苏报告”写出以后,我由长春返回北京,这时,已是炎热的七月了。
二十二
回到北京,稍事休息,由我向乔木同志作了两次访苏汇报,之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交了书面报告。根据中央指示,便着手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从党内系统来说,科学院属于中宣部直接领导。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中宣部科学处。科学院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事先通过中宣部向中央请示汇报;党中央对科学院工作的指示精神,也通过中宣部传达给我们,再通过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行。科学院的最高会议是院务会议。每次开会都是郭沫若同志亲自主持。郭沫若同志对科学院的工作十分重视、热情。我和郭沫若同志早在一九二七年武汉大革命时期就认识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我们参照苏联科学院的作法,首先采取组织措施,设立了学术秘书处,委托钱三强同志和武衡同志负责组建,选人的标准是:一、年青能干的科学家,包括各个学科的人才,如柳大纲是搞化学的,张文佑是搞地质学的,叶笃正是搞气象学的,叶渚沛是搞化工冶金的,还有贝时璋、钱伟长等,都是知名的科学家。二、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当时,在我们的科学家中党员很少,整个秘书处十几名科学家中,党员很少。事实证明,这些科学家都是很好的同志,后来绝大部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国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不久,又建立了各个学部的办事机构,恽子强任数理化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过兴先任生物地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赵非克任技术科学部党员学术秘书,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员学术秘书。院学术秘书处建立以后,首先抓了科学各学科的调查摸底工作,他们经过各个学会,对于各门学科进行了摸底,感到问题很严重。我国过去大都是些轻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化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力学也有一点基础,但很落后。重工业方面问题更多。有些新技术,如半导体我们根本不知道,只知道锗是从烟囱里弄出来的,却不知道怎么用。电子学根本没有,高分子也很缺乏,搞植物学的人最多,但都是搞分类学的,连研究真菌的都没有。地质学方面有点基础,李四光同志抓得很紧,但是比起一五六项建设项目的要求,相差甚远。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地质资料都远远不能满足。总之,我们好多门学科没有,有些学科有点基础,也是少这缺那,很不完全。这就是我们的家底,了解了这个家底,就心中有数了。这对以后制定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于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摸底,对每一个人的学历、经历,有哪些论文、著作和专长,都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证明,绝大数的人有真才实学,也有在理论上能行,实践上差劲的,还查出了极少数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这一查,心中有数了。在实际工作中,就能作到区别对待,量才使用,扬长避短,实事求是。
对科学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刘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表示赞同。在会上,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一再强调了要做好团结科学家的工作。后来,中央又专门就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了批示。中央对科学院的工作很重视,很支持。这时我向西北局指名调两个同志到科学院来工作,一个是郁文同志,一个是柯华同志。郁文当时在新疆办报,任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调来后任科学院人事局局长。柯华当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秘长,暂时离不开,调来后又被外交部要去了。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首先召开了科学院党的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接着抓了科学院建院工作和建立学部及学部委员会的工作。这里说的建院,首先是找地方,盖房子。当时北京市长是彭真同志,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梁思成同志,他们对科学院的建设非常关心,热情技持。一开始,他们提出要把科学院的大楼盖在北郊的黄寺前后,为的是使之与天桥、前门、三大殿、景山、钟鼓楼,用一条中轴线串起来。有点象过去建立魁星阁的做法,放在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他们把图纸拿来,让陈毅同志、郭沫若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考虑到那里是旧城郊区,既没有电,也没有地下水道,又浪费时间。后来,党组研究决定把科学城建在中关村,靠近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那里地下水道、煤气管道都是现成的,建院比较方便。而且,搞一些学术活动,交流情况都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科学中心。北京市委也很慷慨,干脆把中关村,一直到西直门、大钟寺那么一大块地方都给了中国科学院。这时,科学院采取了一项措施,原有的科学单位尽可能的不搬家。这条经验是在长春作调查时取得的。科研单位不要轻易搬迁,一搬迁就要耽误很长时间的科研工作。当时毛主席提出要“超英赶美”,时间就是速度,所以先在全国设立三个分院:上海分院,包括南京科研单位,东北分院,包括长春、大连的科研单位,西北分院,几乎是平地起家建起来的。各地对分院的建立都给了很大的支持,保证了各分院的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建设科学中心的同时,还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的情报研究所,扩建了图书馆。情报研究所所长是袁瀚青同志,他很热心此项工作,订购了很多资料,苏联的,英、美、法等世界各国的杂志期刊都订了。而且在收到邮件以后一周内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研究室,工作效率很高,充分发挥了情报工作的作用。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头脑发热,不讲科学,把情报所也交出去了,甚至将已经继续招考了两年之久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也曾被取消了。实践证明,这是作了一件大蠢事。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实在可惜!
关于在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会的工作,在设立学术秘书处时就开始了。由于对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进行了摸底,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全院设立了四个学部物理数学化学部,生物地质学部(包括医、农科),技术科学部(包括工业应用、工程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部机构成立以后,把名单一公布,科学界感到震动。科学界的重心就进一步倾向于科学院了。在这以前,认为科学院是共产党办起来的,并不懂得科学。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到科学院来,其目的是要钱,要人,要编制,要房子。个别人还以科联和科学院分庭抗礼。学部成立,他们看到学部委员都是科学家,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名字,这一来他们觉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此后,中央又规定了一些照顾知识分子的办法,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三反五反中的某些错案也得到了纠正,影响很大。科联的活动减少,到了一九五七年,科普和科联合并,成立了科协。在这以前,国务院为了加强对科学规划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后来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委,由聂老总挂帅,以政府的名义管理科学工作,名正言顺,从此,我国科学工作走上了正式轨道。
建立了学部,工作很得力,很方便,但是各学部中党员太少,真正懂得科学的党员只有几个,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据当时统计,科学院本部总共只有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十一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因此建党工作也提上了工程。我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要人,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需调到一五六项工程搞建设,党员干部很缺,调不来,安子文同志也无能为力。我只好自己想办法,在北京市找了一些半休养半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干部身体不大好,但是多少还懂得一点自然科学,党的领导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到科学院来可以起点沟通党群关系的作用,还是很有用的。例如,边雪峰同志就是我找来的,后来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又向陈毅同志要党员干部、陈毅同志对科学院的工作十分重视,他说你这一摊子比一个方面军还难搞,我给你从复转军人中找些
干部吧,后来果然调来了一批。此外,我也学习在西北局团结使用党外人士的经验,直接依靠科学家,对他们信任、尊重、放手,鼓励他们主动的积极工作,这办法果然有效。
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召开学部成立大会之前,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回访我国,同时,也是应邀来参加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团长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冶金专家巴尔金。巴尔金到达北京以后到北京医院查身体,医生作了检查后向领导汇报,说巴尔金的心脏病很严重,随时都可能死去。陈毅同志听了很紧张,把我叫去,交给我两项任务是陪同巴尔金访问,要照顾好,不要叫他死在中国;二是抽一些人跟着他,向他学冶金技术。随同前往的有,冶金部副部长刘彬同志,东北金属研究所所长李薫同志,搞化工冶金的叶渚沛同志,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同志等人。我们跟巴尔金从北京到南京,又到上海、杭州,然后又由上海到长沙、太原、阳泉转了个大圈子。巴尔金不愧是个“高炉大夫”,他每到一个钢铁厂,不管多高的炉台,都要爬上去。那时,我们刚开始建设高炉,经常出毛病,不是结渣,就是出不了铁水。请巴尔金一看,很快就找出问题,炉口高了、低了、大了、小了,照他的意见一改就好。巴尔金在中国转了一个大圈,东跑西颠,不但没死,什么大病也没有发生。这里还应当特别说说叶渚沛这个人。他是福建人,曾留学南美,是冶金、化学的多面手,他很注意冶金工业的综合利用,认为矿石都是综合体,除了炼铁,还应当把其他的东西也收了回来。解放初期,他在冶金部工作,宣传自己的观点,因和苏联的一位专家意见不一致,因而不受重用。吴玉章同志就把他推荐给我,于是就留在科学院工作,这次陪同巴尔金参观访问,收获很大。巴尔金曾经看过叶渚沛的学术论文,对他很尊重。巴尔金回国后,我对叶渚沛同志说,给你成立一个研究所,由你调人,他非常高兴。后来,他在石景山钢厂附近建了一个小高炉,定名为化工冶金研究所,这可有用武之地了。以后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在参加攀枝花矾钛矿的建设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个很有贡献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是苏联特务,把他整死了,实在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期间,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领导同志都坐台下听科学家的发言,体现了党对科学和科技人员的尊重和重视,使到会的所有科学家深受鼓舞。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影响很大。会后,在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许多华籍科学家都陆续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着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就是这时回来的。这批科学家回国,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科技队伍,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对头,注意了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政策也比较稳定。看来,这是一条规律,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争取在十二年内在各个主要学科方面赶上或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口号。
一九五六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以及对我国科学现状的调查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出发,迅速制订一个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这就是后来制订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叫“十二年规划”。当时,我们的家底很薄,国际许多先进的尖端的东西我们没有,原来的一些东西发展得也不平衡,为了解决国家大规模建设事业的长远需要,在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时,我们遵循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方针,既认真考虑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又不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大体说来,科学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关主要应该解决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则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理论问题,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搞这个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根据总路线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任务带科学”。这个口号自然有一些局限性,比较侧重应用,这也是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后来为了吸取苏联制订科学规划的经验,还特别请来一位苏联总顾问拉扎连科。他本人是搞技术科学的,专业为电火花加工,而且他自己曾经参加过制订苏联科学院科学规划的工作。他给了我们以十分有力的帮助。当时,给我和拉扎连科之间当翻译的是赵同同志。赵同同志在制订“我国十二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中是起过重大的作用的。但这个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完成,主要是科学院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后来实践证明,这个规划基本上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到了一九六三年,这个规划就大部完成了,其中,不少项目都是提前完成的。由于这一计划实施的结果,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许多学科,如半导体、电子学、原子反应堆等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有的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科学院十二年长远规划制订过程中,我病了,许多人都以为我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觉得不行了。于是,我把过去保存的许多文件、资料作了处理。在病倒以前,我就曾经向分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同志,以及安子文和张际春同志提出请求说:“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不能继续这项繁重的工作,调换一下工作吧”。陈毅同志说:“老马识途,继续干吧”。我说我是老牛破车,拉不动了,再干下去,要耽误工作。经我再三的请求,中央才同意调我到国务院二办,由张劲夫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后来,中国科学界在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提前完成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同时,在聂总的领导下,两弹一星上了天,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我的工作关系转到国务院二办以后,我就病倒了。经大夫诊断说我是疲劳症候群,又说我患有进行性的大脑动脉硬化,建议我到青岛疗养。从一九五六年夏天到一九五七年冬天,我在青岛疗养了一年半。等我回到二办时,林枫同志因患心脏病休息了,二办的工作由张际春同志负责。我回去以后,因考虑到我的身体不好,张际春同志就让我在二办分管卫生、体育工作。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关于我在国务院二办这一时期的工作,了解情况的人比较多,钱信忠、徐运北、崔义田、李达、荣高棠、李梦华等同志都还健在.我就不细说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那就更是大同小异,尽人皆知,我就更加没有必要加以赘述了。
后 记
《庚申忆逝》从一九八一年夏天写起,用了两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现在总算是完成了。关于我写这篇东西的动机、想法和过程,已在去年七月写的前言中,都讲到了。总之,它是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交代材料的基础上,选择、联想和忆述而成的。事物的辩证规律是这样的,坏事往往也会走向它的反面,使我将许多自己的陈年旧账,也不得不被迫苦思冥想地交代一番,否则我是写不出来的。
一九八一年的六月,我到太原,通过山西省委,向省文联借调了李束为同志,向太原市委借调了黄征同志,由我口述,束为、黄征同志整理,写成了本书的第一稿,即征求意见稿。
去年五月,我征得云南省委同意,又把李束为、黄征同志请到昆明,根据各方提出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写成了本书的第二稿。
第二稿写成后,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委托山西省委的罗贵波同志,四川省委的周颐同志,陕西省委的黄植同志,帮助我向一些原来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对全书作进一步的修改。在此基础上,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又到了太原,请李束为、黄征同志把这些意见加以综合整理,写成了本书的第三稿。这就是今天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的这本书。
正如我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想就我自己所学到的这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总结一下自己所经历过的道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现代史和党史研究工作,为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若干资料而已。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十分严肃认真的工作。因为历史实是客观存在的,来不得半点浮夸和轻率。因此,本书力求在内容、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上都能作到基本上准确无误,符合当时的史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这本忆述历时四年,修改四次迟迟拖到今天才和读者见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尽管如此,本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仍然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恳切地期望读者读后,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正。
张稼夫
一九八四年二月于太原
张稼夫 述
束为 黄征整理
附:
张稼夫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宣传、科技和文教战线的优秀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顾问张稼夫同志,因病于199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张稼夫同志是山西省文水县人,1903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在青年时期就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爆发时,他和进步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青年的爱国行动。1919 年到1923年,他在太原农业专门学校读书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毕业后,为寻找救国之路,曾辗转北京、河南等地,积极投身大革命运动。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任国民军二军学兵队教官等职,并将一批学生送去报考黄埔军校。1927年1月,他到达革命中心武汉,任教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4月,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大革命失败后,受党的委托,张稼夫同志先在武汉从事兵运工作,疏散、安置从前线撤下来的军队进步人士,继而到上海、南京、山西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共党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筹委会书记、山西省工委文教委员。在此期间,他不畏艰险,为扩大党的外围组织、壮大党的队伍、掩护党的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在淞沪抗战中,他领导的党支部同其他地下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支援十九路军,在上海军民中引起很大反响。由于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使屡遭破坏的南京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在山西同新闻界、文化界建立了广泛联系,为我党占领宣传阵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张稼夫同志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在运城扩兵工作中,他通过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胜利完成周恩来副主席向省委提出的为一一五师和一二零师“二十天扩兵三千人”的特急任务。1939年春,他受区党委的委托,到延安汇报开展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毛主席还亲自写信表扬了由他主办的区党委《五日时事》小报。他在壮大晋西南党组织、建立政权工作、统一战线和理论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创建和发展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0年晋西事变后,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区党委,张稼夫同志任宣传部长。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他为保障中央所在的陕北根据地的安全和物资供应、建立晋西边区民主政权、粉碎日军扫荡、加强宣传工作和文化建设,历尽艰辛,很好地完成了任务。1940年9月,张稼夫同志奉命到延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任南方组负责人,他根据自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写出研究报告,为党中央制订敌后工作方针提供了重要资料。
1942年底,张稼夫同志调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工作,先后任敌工部长、宣传部长、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他到任后在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在延安约见他时所作的关于壮大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对敌斗争政策、领导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指示,会议决定了“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三大任务。经过晋绥党政军民近两年的工作,使晋绥边区形势基本好转,边区人口由困难时期的不足一百万扩展到三百万以上,人民生活和部队供应都有了明显改善。张稼夫同志为晋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47年春,晋绥地区土地改革中一度出现“左”的偏差,他以革命者的坦荡胸怀对待不公正的批判,同时严以律己,要求到基层做些实际工作,后被批准调任晋南工委副书记兼临汾县委书记。毛主席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晋绥地区“左”的偏差,并肯定了土改初期由他主持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这一文件。
1949年,张稼夫同志任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后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主任。在此期间,他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发展西北地区的文教事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西北局领导下,他为解放大西北、参与制订西北地区民族、宗教方面的具体政策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2年,张稼夫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翌年,他参与领导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了解和学习苏联发展科学事业的经验和商谈合作。代表团回国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设立学术秘书处、组建学部、选聘学部委员、组建科技情报所、建立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建立研究生制度和颁发科学奖金等意见,都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对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受到中央重视。中央对这个报告的批示,全面提出了党的科学政策,不仅对科学院,也对全国科技战线具有深远影响。他还对以后制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做了准备工作。。他主持筹建了一批新的研究所,并组织全院力量为经济建设服务,作出了显著成绩。他积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家建立了亲切的朋友关系,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了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张稼夫同志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科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张稼夫同志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主管卫生、体育工作。他坚持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强调要搞好工厂、农村、部队的医疗工作。他积极倡导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坚持中西医结合、西为中用的方针。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组建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他关心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文革”中,张稼夫同志遭到诬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坚持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党性。
张稼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79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稼夫同志退居二线后,仍不顾年迈体弱。怀着“在有生之年把过去曾大力抓过的若干问题,尽可能做些调查研究,向党做个交待”的夙愿,曾先后对大西北、大西南、横断山脉地区及黄河中下游进行了考察,并就以上地区的综合治理、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多次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国务院及有关部委领导送交了考察报告,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他关心党的事业,为祖国的振兴繁荣沥尽了心血。
张稼夫同志为党、为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分明。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刚正不阿。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干部,团结同志,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爱戴,深得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