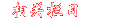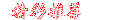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五卅运动中的父亲(06月10日)
- 云霞归来(06月10日)
- 北坡---我人生的第一个家(06月06日)
- 泥巴坨的传说(外一篇)(06月04日)
- 江姐革命引路人戴克宇去世(05月31日)
- 热血忠魂 (下)(05月30日)
- 热血忠魂 (中)(05月30日)
- 热血忠魂 (上)(05月30日)
- 晋绥艺术家--牛文(1)(05月29日)
- 忆我的父亲王其祥(05月28日)
回忆我的父亲龚逢春
发布日期:2016-11-25 13:27 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 作者:龚文章
龚文章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几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三十年的深情厚意,永远温暖着我的心,三十年的谆谆教诲,时时激励着我奋进,每当我思念父亲的时候,历历往事在目,仿佛又回到那流逝的岁月……
1949年11月,我的家乡刚刚解放,我去汉中准备报考陕南,同时也想找一份工作做。有一天凌晨,我的二舅突然从城固来汉中找我,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你爸爸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仍在梦中。因为“爸爸”这个词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和亲近,又是那么陌生和遥远。据说父亲是1932年离开家乡的,那时我还不到三岁,对父亲可以说连一点印象也没有。在我懂事以后,只是听到大人们私下传说我父亲在外面参加了共产党和红军,是被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由于当时环境险恶,父亲一去十七、八年,从未与家人通过音信,我们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是否活着。父亲走后,是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拉扯大(母亲于1950年底病逝)。全家人在苦海中一年又一年地盼啊盼,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二舅又告诉我,父亲是前一天带了一些解放军到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托一个老乡带信回家,母亲带着家里的人赶去见了面。父亲当天就要来汉中,特意叫二舅来找我。当天下午,我在汉中城东门等侯父亲的到来。在我的心中,对父亲一直就充满着神秘感和敬意感,想象中的父亲是高大英武,气度不凡的。这时,一辆美式小吉普和一辆中吉普停在了路边,小车上下来几个人。我看到其中一位年长者,中等身材,穿一身解放军军装,从相貌上看很象我的叔叔,我心下已猜到八九分。他看见我,微笑着问;“是资平(这是当年父亲给我取的乳名)吧?”看到旁边的人都在笑。我十分局促,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当晚我跟父亲住在汉中军管会里。那时条件很简陋,我和父亲同睡一张床,合盖一床很薄的行军被子。天气虽然很冷,我的心里却热乎乎的。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带我睡觉,尽管我已是二十岁的大小伙子了,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了父爱的温暖。由于初次见面,我找不到适当的话题,但又想和父亲多说几句话。于是我将身上穿的小棉衣撩起给父亲看,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件衣服。这件衣服是母亲用父亲当年穿过的一件旧衣服改制成的。父亲抚摸着这件旧棉衣,深情地对我说:“等到革命彻底胜利了,老百姓的生活和购买力就会不断提高,就能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接着,他又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从父亲的谈话中,我头一次知道了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消灭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等道理。虽然他讲的有些东西我听不懂,如“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等等,但有一点我明白了,那就是这么多年来离乡背井在外面所干的事业是非常伟大和崇高的。父亲的形象在我面前突然变得十分大。谈话中父亲也问到了我的学习情况,他鼓励我坚持把高中念完(因那时家境贫寒,全家只供我一人读到了高中),争取再上大学,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劳知识的劳动者,作为一个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将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那晚父亲兴致很高,一直谈到鸡叫,尽管我见他因劳累而不住地咳嗽。末了父亲告诉我,人民解放军已兵分几路入川作战,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明天他们又要踏上南下征程,成都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与父亲的第一次见面,是我人生征途上的一个里程碑,一瞬之间,我仿佛长大了许多。
1950年,我考入成都石室中学;1952年考入四川大学,直到1956 年毕业,在父亲身边渡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在这期间,我耳濡目染父亲的一言一行,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使我对父亲有了较深的了解。我在成都念书时是住校,逢节假日才回家去。父亲在川西区党委工作时,机关食堂吃饭分大、中、小灶,开始我回家时有人叫我去和父亲一起吃小灶,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说领导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要我去大灶吃。因而我一直都很自觉地在大灶吃饭。刚解放时,组织上给干部子弟也发干部制服穿,在当时穿这种制服是很显眼的。父亲考虑到我正在念书,应当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哪怕在穿着打扮上也不能有“特殊”的表现。于是父亲用自己的一点津贴和保健费(那时未实行工资制),按学校同学的服装样式给我做了一套学生服。我在念大学期间,父亲每月给我的生活费都是精打细算了的。除去必要的伙食费外,剩下的钱也仅够理发和买点牙膏、肥皂及文具的了。他还特别叮嘱妈妈不要背着他多拿钱给我。他对我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有些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困难,你现在已经很不错了,要保持在家乡时的艰苦朴素作风,生活好了,不能忘本啊!”父亲的话对我震动很大,我也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决不给父亲丢脸。一些当年和我同学的人至今都说我那时是一个带乡土气息的学生,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优越感。我想,这与父亲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还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突然问我:“你来成都上学半年了,习惯了吗?认识不少人了吧?”我不在意地说:“很习惯,认识了一些朋友,和同学们相处也很好。”父亲却对我说:“成都是个大城市,又刚解放,很复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丑恶的东西仍然存在。”他提醒我结交朋友要慎重,千万不要被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迷住。父亲的一席话,给我敲了一个警钟。我在成都念高中时,有一次听父亲的同事说组织上要保送我去苏联留学,很高兴,就去问父亲。父亲对我说:“出国留学当然好,但在国内学习也一样,关键是要刻苦和勤奋,这次你就不要去了。”后来我得知父亲把名额让出去了,他那种无私的精神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父亲虽然长期从事党务工作,但他非常关心我国的农业发展情况。1952年我报考大学填志愿时,特意征求父亲的意见。他毫不犹豫地说:“报考农林专业。”就是父亲这句话,决定了我的终身事业。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四万万多人的吃饭穿衣,都得靠农业,而我们的农业生产还很落后,需要很多农业科学家,你来自农村,学到了文化知识,应当回到农民中去,为他们服务。后来我考取了四川大学农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技术工作至今。解放初,我姐姐和哥哥想请父亲帮助进城参加工作,父亲对他讲:现在刚解放,城市里也有很多人需要就业,农村很快就要进行土改,你们可以分到土地,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如果都不愿意当农民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呢!父亲勉励他们安心农村,搞好生产,为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四十年过去了,我姐姐和哥哥一直扎根在汉江之畔那块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上。为了了解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父亲曾专门找我借阅“农业发展纲要”。有一年他听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苏联土壤学家威廉士及其土壤学,就仔细阅读了《威廉士的土壤学及其发展近况》一书,后来他把这本书寄给了我。并且嘱咐我:“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土地,你是搞农业的,首先就应当精通土壤学。”至今我仍然珍藏着这本书。
在工作上,父亲总是要求我们作子女的无条件服从党和国家安排,积极多做贡献,同时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给予关怀。大学毕业后,我和爱人一起分配到北京中央农垦部设计院工作,主要担负着我国大型农场的勘测设计任务,经常要跑边疆。那时我们的孩子很小,夫妇俩一出差,孩子就成了大问题。父亲知道后,一方面要求我们坚决服从革命工作需要,同时叫把孩子送回成都他身边来抚养,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就这样,我们的大海子从不满周岁直到快念小学,都是在爷爷奶奶身边渡过的。那几年我们每月给孩子寄去生活费,但父亲和妈妈一分不动地替我们如数储蓄下来,到1962年我们接孩子回北京时,父亲和妈妈便将这笔钱“退”给我们了,我又一次体验到了父亲那伟大而深沉的爱,大约是1960年吧,父亲要做胃部手术,他的胃病是战争年代就患上了的。我很挂念父亲的病,准备请假回成都照料他,单位领导也催我快走。正在此时接到父亲来信,他说国家农垦事业发展很快,有很多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完成,不能因他的病影响我的工作。在父亲的坚决阻拦下,我只得坚守岗位,写了信去慰问他。后来我得知,父亲在那次手术中,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农垦部设计院要抽调大批干部支援边疆和内地的农业生产建设。我当时想回成都,父亲来信叫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听从党的召唤。开始听说我要去新疆,父亲特地为我们一家准备了一些御寒衣物。后来我去了湖南洞庭湖区,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几年。父亲在我去湖南不到半年,也调到北京中央党校工作。当时父亲和妈妈身边无子女,我的三个妹妹毕业分配工作都是服从国家需要,没有一个留在父亲身边。只是到了父亲晚年病重住院,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料,他才不得不同意组织上把我的两个妹妹调到北京。父亲在工作和生活上支持和关心我的同时,在政治上也要求和鼓励我不断进步。有一次我升了一级工资,很高兴,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回信说:目前国家还处在“恢复时期”,能拿出钱来调资很不容易,你能评升一级工资是组织对你的关怀,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多做贡献,少讲报酬。为了帮助进步,父亲买了很多马列原著寄给我,要求我认真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鼓励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大期望,因为他毕生都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在奋斗。1964年我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由于“文革”中“左”的思潮的影响,我的入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尽管这样,我始终按照父亲的勉励不断追求。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我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看到这一天。我只有默默地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先是批斗和非法关押,后又被下放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先软禁,后又带病看菜地。父亲虽然身处逆境,但是他从不对我讲自己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总是教育我要认真学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1972年1月,我们全家到河南去看望父亲和妈马妈和外婆三个老人住的是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子,用水是到100多米远的一日辘轳井去抬,生活极为艰难,看到那样的情景,我们都流下了眼泪。然而父亲并未因此消沉下去。在我们去探亲的那些日子,父亲常常给孙子孙女讲革命故事,有时还给大家讲几个民间笑话,尽量缓和我们压抑的情绪。有几天还听见他哼起了陕北民歌,我知道他又在回忆自己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时的战斗生活。每天清晨,我都看到父亲顶着凛冽的寒风,迎着初升的太阳,昂首挺立在广阔的平原上。
1978年11月,我出差到北京。父亲的病已很重。在医院他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每天收听新闻节目,阅读书报和文件。前来探望他的中央领导和老战友都对他说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但他总是说自己剩下时间不多,还想为党做点工作,不学习不行,有一天他还特地询问襄渝铁路和阳安铁路的建设情况,说是病好了要回城固家乡和四川看看。然而,父亲的这个愿望已无法实现了。12月1日早晨,我和妈妈守候在父亲的身边,看着他——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静静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他的枕边,还摆着一本未看完的书。
1991年5月于成都
作者是龚逢春的二儿子、四川省农牧厅高级农艺师
资料来源:《龚逢春纪念文集》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1993年12月出版
本站编辑:杜瑞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