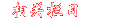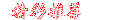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永远的牵挂 共同的情怀(04月06日)
- 关向应图书馆建馆80周年纪念活动在山西兴县举行(04月06日)
- 在延安精神的旗帜下(03月29日)
- 林炎志: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03月03日)
- 老区孩子们的一份承诺(02月24日)
- 北京汇文中学“贺龙班”成立 全国招生贯通化、一体化培养田径人(02月23日)
- 怀念一位百岁晋绥老前辈(01月27日)
- 家中吊唁蹇阿姨……(01月03日)
- 他是最后一位亲历者(11月28日)
- 永远和老区人民在一起(09月09日)
绛地晋缘
发布日期:2016-11-30 10:33 来源:三晋都市报 作者:三晋都市报

绛县晋文公墓
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遗迹遗存丰富的“侯马晋国遗址”夯实台基,有《左传》载“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迁都于彼的文字和“侯马盟书”佐证,故尔早已旗正标明为史界公认;但晋国始封地“唐”、晋早期邑都“故绛”却一直众说纷纭,难以落定尘埃。对此,史学界一直有两种声音。
其一,因水而地。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载,“唐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照此脉络,先后有晋阳、平阳、翼城等多种说法,但众声喧嚣后终未有定音。2007年一件铜簋的面世,使史学界有了“因地而水”的又一种声音。
铜簋铭曰“王令唐伯侯于晋……”据此,考古专家推定,是唐伯燮父接受了周王的命令由唐而晋,晋即由此迁于新田的故绛,晋与唐是晋三都两迁中的两地。但照此而往的远眺中,似乎寻根路径仍难以厘清。
在漫漫的探索中,有专家发现,“晋”与“绛”是周语和晋语对同地、同名的两种读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田建文教授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中专门对此做了阐释。也就是说,专家认为,“绛”即是“晋”,“晋”即为“绛”,晋绛同宗同脉。把“绛”作为考证“晋”之地望的入口,许多羁绊便水到渠开。
绛县于是跃然于考古、史学家视野。虽然在几度地迁名移、疆融界易中“绛”之地理坐标和人文内涵都在变化,但,源头之“绛”中蕴含的晋之基因总是无可辩驳的。
这对由于缺乏足够信史支撑,总被排在晋之边缘地带的绛县而言,不啻于柳暗花明的一个导向。
晋地有晋水。
绛县境内有两大水系。一条是以大交镇东浍水二源之一“浍交”为枢纽的浍水系;一条是源出陈村峪,汇集紫家峪和冷口峪诸河之水的涑水之脉。
两大水系,两条对话源头的脉线,两条连通晋史的河道。
浍水系以浍交为坐标原点,上接里册峪、磨里峪、续鲁峪诸水,所谓“诸水交会”,沿途河岸一路散落着因晋文公驻兵而得名的东、西、北晋峪村,以及“晋峪泉”“晋水庙”“晋堂水”等“晋”字标号的“路牌”;沿磨里峪一支上行,又一“晋”字号的村子——大晋堂村,水淙木幽处一泉杳然,人称“晋源泉”——这里,果真倒映着数千年之深的晋之史吗?兴奋之余不禁令人更生几多期盼。
由浍交而下浍水一路蜿蜒了去,是“晋人谋迁新田,谓有汾、浍以流其恶”的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也就是说,绛地“浍交”之水,即使不是一水之下易唐为晋的晋水,也是导引着晋国易都迁址并沃灌了其十世200多年历史的吉水沃泽。
再看涑水一脉。
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周威烈王时,韩康子都平阳,从智伯伐赵,决晋水灌晋阳。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桓子时韩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也。”又,《志》云:绛水西流,入闻喜县,为涑水之上源。
安邑在今夏县禹王城,战国时为魏国所在地,能灌安邑(魏国)的自然是涑水河了。虽然此处所言“上源之绛水”,远非“源出绛山,扬波北注”,最终汇于“浍河”有“白水”“沸泉”之称的“绛水”,但按照“绛”“晋”同源的说法,也许正隐含了“晋地有晋水”的原始指向;亦虽然“涑水”之脉终未能如“晋水灌晋阳”那样灌开如“三家分晋”般的一条史河,但也足见其在晋史中的大脉要流之位。
晋水是晋地的“网络”链接。《史记·晋世家》云,“(献公)八年,士蒍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读史方舆纪要》载,“聚,即今山西省绛县东南十里之车厢城。”
据此,如果说车厢即晋都“故绛”仍然存疑众多,迷雾重重的话,可以将关注的目光由车厢城南北望,那里有直抵周王朝镐京、洛阳旧新两都的轵关陉。仔细倾听由此过往的辚辚历史车鸣,或许可以廓清由车厢而故绛的原始路径——
“文公勤王”是晋从众诸侯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一环。想当初,“尊王攘夷”的猎猎义旗下,文公重耳以轵关陉为捷径,一路越关渡河,平叔带之乱,护襄王复位,不仅提升了晋在周王朝的“国际”地位,扩营收地的同时也尽将轵关陉全线收入盘中。
又是在轵关陉,三年后,又有数百乘车辚马啸,晋文公由此而往会战强楚,留下“退避三舍”美谈,写下奠定霸主之位的城濮之战史话,随之,又经“践土会盟”由“侯”而“伯”霸而名至实归。
还是在轵关陉,成就了“绛商”,进一步打通了“绛”与“晋”的链接:《国语》记载,“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
绛商之富,在于发轫于晋晚期都城新田的铸铜业,而从铸铜基地到中条山垣曲铜矿之间铸铜原料的运输和成品的回送都是经由绛县轵关陉进行的。因铜而富,富的自然是“晋商”与晋国。铜,奠定了文公称霸的经济基础,由绛商而晋商,“绛”“晋”同源再添佐证。
再往前推,还有“曲沃代翼”“文侯勤王”等多重晋国的历史剧目在这里上演。一浪又一浪的历史回声均昭示着,绛与故绛、绛与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剥茧抽丝中是否也可以说,故绛之谜团可以经由绛县轵关陉散结解绾?
由轵关陉更广一些放眼,县境内随处可见历史疾驰中扬落的碎片——
有献公之子卓子隐居于其的卓子沟,有晋国祁午将军练过兵的小祁村,有晋史官董狐的封地董封村,更有“献公”“文公”“灵公”三公墓……
一个遗存一个标签,一段传说一个指向!由此一路追溯了去,关于晋之始封地“唐”,突然有了这种遐想:司马迁当初之所以没有工笔细描地具体指点,而只是“河汾之东方百里”的一个大写意,也许正是要给后人伸展一个“大晋国”下的大视野:原本“河汾之东”就都是“唐”地所在,“方百里”内都有晋人活动的遗踪。不是吗?历史是网状分布的,而不是线性游移。正如“晋”之缘亲“绛”,境内泉丰水沛,河网纵横交错,你能说哪一眼泉不是历史深情的凝眸,哪一支流没有一路过往中岁月淙淙的留声?
绛县之于晋,也许就是瀚海之于源泉,但要码足其在晋史中的权重,还要进一步深挖细掘,更多地拥有诸如“侯马盟书”一样的重量级的砝码。(刘云霞)
本站编辑:杜瑞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