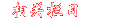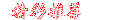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有这么一批《晋绥日报》的传承人(07月10日)
- 浇开中朝友谊之花(07月09日)
- 有一种记忆叫怀念……(07月08日)
- 有份爱心来自大唐(07月04日)
- 播撒慈善的种子(06月28日)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甑家庄战斗之花子村战斗
发布日期:2016-02-03 16:12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黄其云
甑家庄战斗之花子村战斗
---黄其云革命回忆录摘选

前排右一为黄其云与长女白山杉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日寇八十五大队七百多,伪军一百多,骡马、民夫三百多,从白文镇、寨子两路出发,窜入兴县进行残酷的扫荡。敌人的目的是破坏秋收,残杀人民,以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晋绥军区在贺龙将军的指挥下,针对敌人的“扫荡”,计划以三区为主要战场,在好几个村镇都设有埋伏点,一步一步地诱敌进入包围圈,然后一举歼灭。
就在军区大力部署,即将诱敌深入的关键时刻,我从一区调到三区。区委书记马柏树同志抱怨县委不该在这种战斗紧张的节骨眼上调来一个女同志。他想把我安顿在一个安全村庄的老乡家中,以等待这次反“扫荡”的胜利结束。我极力反对他的这个主张,坚持要求和他们一样到前线配合作战。
老马说服不了我,便宣布散会,随后就和区委会的几个同志分头下去了。临走,给我留了几句话:“明天上午白县长要来三区,检查战备工作,等他来了,区委再一起研究确定分工,看哪里既能工作又能保证安全。”
我听了哭笑不得,可也没有办法,只有耐心地等明天。闲着没事,就找通讯员和炊事员聊天,了解这几年敌人“扫荡”和我们反“扫荡”的情况。他们提起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实行的“三光”政策,立即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讲开八路军军民团结一致抗日,从四○年起进行了六次反“扫荡”的斗争,则眉飞色舞,喜气洋洋。
小通讯员说:“我知道你想参加战斗,咱老马胆小怕事,不敢点头让你去。明天白县长来了,你求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的。”
老炊事员补充道:“白县长那人可威啦,连贺老总都喜欢他,他领导兴县人民打日本,既胆大又心细。你明跟他说,只要有个熟悉情况的同志跟你一块,就能保证不会出问题。”
我根据他俩的指点,第二天在会上向白刃同志提出,请求让我和一个同志一起到前线去锻炼。白刃同志欣赏我敢于要求上前线的精神,他对马柏树说:“我看她精神可嘉,你就指定一个同志和她一起去吧!”
老马连忙说“好”,并指定赵洪则负责带领和照顾我。赵洪则,区委组织委员,政治上忠实可靠。他是三区花子村人,地理环境很熟,群众关系好,一接受任务,就很诚恳地说:“小黄,你放心,有我保驾,不管走到那里,都保你万无一失。”
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已经心满意足,对他的讲话。只含含糊糊“嗯”了一声,便一股劲催他早点出发。
一路上,还不断地催他走快点。他说:“我走快了,怕你赶不上。”
我说:“咱们试试看。” 。于是他甩开手,快步流星往前走,我毫不示弱,踏着小碎步,紧紧跟了上去。就这样,一口气走了七、八里,他才放慢脚步,边走边说:“看不出,你走路还有两下子。歇一会儿,咱俩再比赛一番好吗?”
我答应了一个“好”字,立即一个箭步窜到他前面,如飞似箭地奔走起来。赵洪则一面追,一面喊:“小心,别跌倒。”可惜当时没有手表,不能准确地计算我们行走的时速。不过依我估计,那二十来华里,顶多花了一个小时,就是多也多不了十几分钟。
我们到达曹家坡,正巧遇见侦察民兵回村报告情况。他说日本鬼子正在小善畔山头焚烧尸体,看样子当天晚上可能准备向东南方向突围。赵洪则立即喜上眉梢,笑眯眯地对我说:“咱们来得正是时候。”紧接着就把民兵干部召集在一起,检查枪枝、弹药和手榴弹,确定傍晚各自带领民兵进入埋伏阵地。
那天十月六日,已是日寇进入兴县“扫荡”的第十天。这十天,鬼子到处碰壁挨打,饱尝了我军民反“扫荡”的威力。首先在黑峪口,吃了河防部队一顿炮弹;随后又在逃往小善途中,遭到民兵的几次反击;再就是在小善畔被我军阻击,敌人因伤亡过大,被迫退守高地而陷入我包围圈。
那晚皓月当空,赵洪则带着我察看了全村所有的埋伏阵地。百多民兵分散隐蔽在曹家坡两面山头上,一个个睁大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山下那道川。只要鬼子一出现,马上就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我第一次看到民兵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有一种必胜的信心。想到自己即将和他们并肩作战,心里真是万分高兴,恨不得立刻就能举起枪来瞄准敌人。
正巧这时候,一个民兵问我:“黄同志,你打过仗吗?”
我回答:“没有”。
他又问:“害怕吗?”
我实事求是的回答:“不怕。”
赵洪则瞪了那民兵一眼,说:“黄同志是从领导和指挥咱们抗战的延安调来的,你问这些干什么?”那民兵吓得一缩脖子,吐了吐舌头,好像想说几句道歉或请求原谅的话。我一摆手阻止了,并说了句:“问问有什么关系。”
赵洪则没有再说别的,便领着我进入我们的阵地。这阵地位居于两面埋伏点的中间,山头人员少,很明显地是这次行动的指挥点。侦察民兵来回报告敌情,眼看鬼子一步一步离曹家坡近了,民兵们更加紧张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可赵洪则却指着一块大石头,叫我坐下休息一会儿,他说:“等鬼子踏响了地雷,你再过来打枪扔手榴弹也不迟。”
我没有听他的,他好像还想再劝劝我,不料西北方向已传来了“轰隆──轰隆──”几声巨响,接着人叫马嘶,一阵混乱之后, 又响起了机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民兵侦察员跑过来报告:“鬼子踩上地雷,被八路军追下来,正在向咱三区败退。”
赵洪则马上下令叫打,并且大声说:“叫小日本再尝尝咱三区民兵的利害。”说着,他给我两个手榴弹,告诉我看准了往日本鬼子堆里扔,千万不要扔在民夫群中。
我刚一答应,就看见已经挨了十天打的日本鬼子,有的拖泥带水,有的跑掉鞋不得不赤着脚,一个个步履艰难地出现在曹家坡两面临山的大川里。
这些疲于奔命的鬼子兵,正想松口气放慢一下脚步,又遇上了三区民兵的严重打击。一刹时,枪弹、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山川,鬼子的嚎叫和骡马的哀鸣同时并起。一阵猛烈的响声以后,吓得手脚无措的伪军和民夫,僵卧在地上连动都不敢动,那些匍伏着的侵略军,更是到了不知自己是死是活的境地。
这时突然有人喊了声:“土八路”!一个鬼子军立即闻声而起,嘴里“唔哩哇啦”叫喊了一阵,便命令那些刚爬起来的伪军和日本兵往山上冲。
赵洪则笑着把手一挥,站在我身旁的十几个民兵立即簇拥着我,向后面的山沟奔了下去,剩下他和三个民兵还站在那里,等着一群正往上爬的鬼子,又请他们吃了顿子弹和手榴弹,才从容不迫地滑下山来,对我和民兵们说:“走,回去睡觉去!”
我望了望两面山头,问:“还有那么多民兵呢?”
赵洪则神秘地一笑,说:“早转移到刘家庄等候日本鬼子去了。”
我又问:“那咱们为什么不去?”
洪则答:“咱们另有任务。”
我追着问:“什么任务?”
他笑了,说:“打扫战场,然后到花子村配合部队作战。好了,说清楚啦,这下总该放心回去睡觉了。”
我一点头,睡意立即随之而上。回到房东老大娘的热炕头,一倒下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天刚朦朦亮,睁开眼就问大娘:“洪则他们来了没有?”
大娘说:“你别着急,他们来了会叫你的。”
我当然不能等人叫,于是连忙下坑洗漱。很快院子里有了响动,随着赵洪则陆续进来了二十多个人,有昨晚参战的民兵,也有今天才见面的老乡。他们有的牵着牲口,有的拿着萝筐扁担,有的扛着铁锹,喊 上我便一起出发了。一路上,人们一个个笑容满面,高声大嗓地谈论昨晚打鬼子的事。
别看这穷乡僻壤的文盲老百姓,可从小在中国中原文化的培育下,口头文学水平却相当高。
这个说:“咱们把鬼子打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那个讲:“鬼子被咱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一个老头说:“小日本孤军深入,进退维谷啦。”
又一个讲:“日本鬼子这次可是陷入咱们的天罗地网,插翅难逃了。”
洪则和我听得津津有味,直到下山进了昨晚鬼子挨打的那道川,他才开腔,具体分配打扫战场的工作。
我的目光随着他的分配转了一个圈,看清了几件该干的事情:一、掩埋尸体,昨晚打死敌人不少,可日本鬼子的死尸都驮走了,剩下的只是几具伪军的尸体,这个任务不重,由六个老头负责掩埋;二、清理驮子,日本鬼子伤亡较大,要把伤号和死尸弄走,便只有将牲口驮的驮子扔掉才能解决。昨晚一战,敌人扔下十来个驮子,有干粮、罐头等食物。还有衣服皮鞋,这些驮子不仅多、重,而且有的炸散了、掉落了,收拾和扛抬起来都比较困难,因而是这次任务中最重的一件活。重活累活,当然应该由十几个青年人负担;三、收拾到处散落的枪支弹药,根据敌人的伤亡比例来看,散落的弹药、枪枝少于伤亡数,很可能是敌人驮走了一部分。由于这部份战利品有限,民兵都想能分到一些,所以争着干这个活路的相当多。
洪则看出了这个苗头,一面分配一面笑着说:“同志们,别忘了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个民兵赶忙表态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全知道。”
另一个接上岔:“我们打下来的,上级总得分给我们一部份。”
洪则说:“分下来当然归你们参加过战斗的民兵。不过,打扫战场时可不许私吞。”
那几个民兵说:“你放心。”
洪则一笑,问我:“小黄,分给你一个任务好吗?”我点点头,他说:“你监督我们清理,把所有战利品,包括枪、子弹、罐头、干粮,一样一样的都登记起来。”我很干脆地答应:“保证完成任务。”我们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完成了打扫战场工作,就开始上花子村。
花子村,建在兴县南川边的一个山坡上,村里有二百多人口,是三区的一个大村庄,昨晚敌人在曹家坡遭我痛击以后,沿川溃逃路过刘家庄、康宁镇等地又遭我同样伏击。七日拂晓,日本鬼子逃到花子村,企图进村稍事休整,不料挨了我民兵和追击部队一顿痛打,并将其逼出村外诱入我设好的包围圈。
敌人走投无路,被迫拼命占领了村外的一个小山头,准备以顽抗来等待救援。但小日本早已兵力不足,只派了五架飞机前来助战,以掩护收容其伤亡溃退的败兵。就在这个时候,洪则引着我进了花子村,村里静悄悄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表面上,简直看不出一点战争气氛。
洪则说:“走,咱们到打谷场上去看看。”
打谷场上,同样无影无声,一片寂静。我说了句:“这里也没有人。”
话音刚落,场边上立即冒出一个老大爷,说:“洪则,支书和村长正坐在你家炕头上等着呢。”
洪则问:“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老大爷答:“担架队的人集合在这里待命。”接着他望了我一眼,问“洪则,你怎么把个女同志带到火线来了?万一有个闪失,可不得了。”
洪则笑着说:“有我这个赵子龙保驾,料也无防?”老大爷说:“鬼子飞机炸了一上午,我说你还是得提防着一点。”洪则点了点头,没有开腔。
我问:“大爷,你们的担架队呢?”
老大爷答:“隐蔽着呢。”于是洪则叫那老大爷引着我们察看了他们的隐蔽场所,原来场边有一条下坡的小路。小路崎岖,既可隐蔽又可转移,不是本地人很难发现寻找。至于我,当然是在他们的引导之下,才发现二十来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和四、五付担架。
老头们一见洪则,纷纷笑着打招呼,还有两个问他回家了没有?老大爷又连忙催他快回去,免得支书和村长等急了。洪则安顿了几句,便领着我来到他家里。果然他娘告诉他,两个村干部等急了,一个叫到民兵埋伏点去找,一个说是在村东头坚壁粮食。
洪则听罢,说:“小黄,你在家里坐一会儿,我去一下就回来。”他不等回答,转身就走。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按他的指示进窑洞,而是跟上他往前行动。他回头一笑,说:“到了战壕里,可得听我的。”
我顺从地答应:“那当然。”但一到民兵埋伏的小山头,刚一看到支书,就听见了飞机低飞的响声,洪则、支书叫我转移到山沟里去隐蔽。我摇了摇头,仍然跟着他们匍伏在山头上。
他望了我一眼,无可奈何地说:“真拿你没有办法。”
支书说:“鬼子都快完蛋了,他的飞机有什么可怕的。”
一个民兵说:“给我一门高射炮,准能打下它一两架。”
又一个接着说:“不用高射炮,就拿步枪也能打它几个窟窿。”他的话没有完,一架敌机便向我阵地冲了过来。这个大胆的民兵果然站起来,端上枪准备射击。
洪则一面打手式阻止他,一面低声对我说:“小黄,别动。看样子,敌人是在搜索尸体和残兵败将,并不是要向我们扔炸弹。”
一个民兵说:“鬼子没有多少炸弹可扔啦。”不出他们所料,敌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大概没有搜索出什么,就夹着尾巴飞跑了。
敌机一走,敌人占领的山头上突然升起一股浓烟。支书说:“鬼子又开始烧尸啦。”紧接着,秋风吹来了一阵恶臭,随后又传来一声又一声地嚎叫。
洪则站起来说:“这帮法西斯连伤兵都烧啦。”
我站起来,望着敌阵地问:“是不是敌人又要准备突围逃跑?”
洪则说:“是的,民兵同志们,咱们可要提高警惕,决不能让敌人从咱们的阵地突围出去。”
支书说:“你放心,要从这里逃跑出一个日本鬼子,你就拿我示问好啦。”
洪则说:“好,这可是你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支书说:“你放心,保证出不了错。”
洪则说:“好,这里就交给你了。小黄,走吧!村长还等着咱们去检查坚壁清野的工作呢。”
我俩回到村里,在村长的引导下,检查了整个村的坚壁清野工作,不仅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好藏好,就连每家每户一日三餐的口粮也都藏得很严实。万一日本鬼子占住村子,也休想找到半顿饭的粮食。
村长笑着问:“洪则,你看怎么样?”
洪则说:“好极啦。鬼子这次彻底完蛋了,就是打不死也得把他饿死。”
我跟着连声赞好,并夸奖他们藏得真巧妙。
村长很高兴地说:“这下你们满意了。洪则,天不早了,你该领着黄同志回家吃饭啦!”经他提醒,我才发现此刻已日落西山,接近黄昏啦,转了一下午,肚子的确已空空如也。
洪则一笑,便引着我直奔家门。他娘早站在门外翘首而望,一见我们连忙招呼我进窑上炕,炕桌上的碗筷摆得整整齐齐,锅里热气腾腾,一股黄米捞饭的香味,立刻引发了我的食欲。我刚一坐下,大娘就把盛好的一大碗饭递到我手里。黄米捞饭上面还加了一层豆面拌汤,还有葱花和几滴香油。
我一面吃一面称赞:“好香,好香。”
洪则娘听了,笑得嘴都合不拢,不停地说:“好闺女,真像咱自己人。”
随后她又像想起了什么,忽然用一种责备的口气对儿子说:“你真是吃了豹子胆,怎么把她带到前线来了,万一……”
这两个字的下文还没有露出来,外面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
洪则放下碗,迅速跑到门口,拉开门就飞快出去了。我跟着跳下炕,准备也出去看看。
洪则娘一把拉住我,说:“你可不敢往外乱跑,等洪则摸清情况回来后再说。”
一转眼,洪则推门进窑,气喘呼呼地说:“鬼子突围了,有一股正向村里跑过来。娘,我和黄同志先走,你收拾收拾也赶快转移吧。”我想等大娘一起行动,但洪则不由分说把我拉着,就往门外奔跑。
这时候,少数胆大留在家里吃饭的夫妇,和个别舍不得离开家的老头、老太婆,相继从家里奔了出来,和我们汇合在一起往外跑去。路过打谷场下坡时,洪则叫大家慢慢地向沟下转移。他引着我去安顿了一下担架队,才去追赶下沟的人们。到了一个深山沟,原来村里有好多人隐蔽在这里,沟外有两个大孩子站岗放哨,沟内一块能遮风的地方躺着十几个老人,妇女们带领婴幼儿紧靠老人们挤在一起。
洪则把我安顿在妇女旁边,便喊着找他娘,想不到他娘竟在他身后,笑着答道:“你不用担心我,还是保护好黄同志要紧。”
我说:“大娘,应该是保护你最要紧。”
洪则娘说:“我一个本地人,到处山沟都熟得很,要他保护做什么,可你不同,是咱区刚调来的新干部,人生地不熟──”说罢,她就催我睡觉。我一倒下,竟稀里糊涂睡着了。
一觉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一阵“喂喂喂”的喊声喊醒啦。开始以为又有什么情况,“蹭”地一声站起来看了看,天上银盆似的大月亮,发射着耀眼的光芒,从山岭一直照射到山沟。隐藏在沟里的乡亲们,全都进入了睡梦之中。再一看,坐在对面的赵洪则却不见了,正想问问他娘,可这时才发现大娘也在呼呼地熟睡,当然不能惊醒她,心想只有走出去问哨兵。
我刚准备抬步往外走,恰巧洪则走回来说:“没事,你别出去。”我问他方才是什么人喊喂?他说是咱部队在通电话,他出去查岗,曾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分析起来敌人可能已被撵回包围圈,因此他放心地叫我继续睡觉。
我已睡够了,叫他安心睡一会儿,由我来负责查岗和保卫大家的安全。说罢我便站起来走出去查看岗哨,岗哨早已换成了两个青年妇女,她们穿着一身破旧的薄棉衣裤,腰上束了一根皮带,手中握着红樱枪,精神抖擞地站在守卫乡亲们的岗位上。看到我,她们像正规哨兵一样敬了个军礼,然后报告“平安无事。”
我和她们一起巡视了一下周围,又站了好大一会儿,仍然是万籁无声。这样看和听,解决不了要知道的敌方确切情况,只有回到村子里去才能彻底摸清楚,可要回村,当然得和赵洪则一块才行,为此想回到隐蔽地唤醒他,不料一转身就看见他笑眯眯地站在我身后,他不等我开口,就说:“我知道你想回村去看看。不过,现在情况不明,回去很不安全,咱们不怕一万,就怕──”
我连忙接过来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日本鬼子占领了花子村,咱们回去就凶多吉少。”
他说:“你既然知道利害,就不能冒险回去。”
我笑着说:“你别危言耸听,咱们还是冷静地分析一下,敌人究竟进村了没有?”洪则笑了,我俩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敌人进村子的可能性小,被我们撵回包围圈的可能性大。两个站岗的女青年也都同意我们的看法。一个说可以回去看看,一个说让洪则先回去,看清楚了没有敌人,再转来喊我,洪则立刻说这个办法好,叫我耐心等一会儿,我不同意,他没有办法,只好两个人一起往回走。
这时候,东方已经开始发白,天朦朦亮啦。一路上,赵洪则指点说,遇见敌人要沉着机智,要善于利用地形,迷惑敌人甩开敌人。他还教我怎样转沟,如何隐蔽。快进村的那阵,又特别告诫,一定要走在他的后面,碰到敌人赶快转身按他指示的方向跑。为了减少麻烦,我连声答应。
我们进村转了一个弯,远远地看见山坡上的一排窑洞前面,站着十几个穿军衣的人,赵洪则连忙指挥我,停住了前进的步伐,而他自己却急步向前,想凑近一些好看个明白。我趁他不注意,还是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发现了,正想责备和阻止我。恰巧这时候,坡上的哨兵喊了声:“口令!”
赵洪则连忙作了回答。坡上紧接着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大声说:“区委会的。”
坡上一阵欢呼,窑洞里又跑出一群人,有二、三十个八路军像赛跑一样地奔下来,把我两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一个说:“可把你们盼回来啦。”
一个问:“你们隐蔽在哪里?我们到处都没有找到。”
另一个讲:“你们坚壁工作作得真好。”
又一个问:“你们的粮食藏在哪儿,我们连一粒米也没有找到。”他们还说,日本鬼子被困在花子村的高地上,已经粮尽草绝,人畜都已饥饿难当,昨晚趁我军略有松驰,便派了十几个鬼子兵准备突围进村抢粮食,这些小日本刚一溜下山坡,就被我部队和民兵发现了,只打了几枪,那些失魂落魄的鬼子便缩着脖子退回山头,一夜都没有再敢动一下。尽管敌人突围不出来,而我部队还是加强了花子村的兵力。
他们从凌晨进村一直到傍晚,还没有找到人和粮,想不到正在等米下锅的时候,遇见我们两个区干部,怎么能不高兴欢呼呢。洪则和我分头引着他们,找到了坚壁的粮食,眼看米下了锅,我俩才去找隐蔽着的一些乡亲们回来。
接着鬼子的飞机就盘旋开了,洪则开始有点担心,怕敌人在垂死挣扎的时候狂轰乱炸,但观察了一阵发现敌机仍然是在搜索,来来回回地寻找什么,尽管如此,还是得提醒和组织群众防止轰炸。
忙了一个上午,下午正准备去看看民兵,恰巧接到命令,调三区民兵去甄家庄接受新任务。赵洪则高兴地说:“咱们要打歼灭战啦!”他立即准备引着我,和民兵们一起到甄家庄去。不料马柏树同志却从甄家庄赶到花子村,宣布军区的决定,计划在甄家庄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把这群鬼子兵彻底全部地消灭在那里。
他说军区首长说:“我们要打得日本鬼子死无葬身之地,叫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接受这个应得的教训,永远也不敢再来侵略咱中国。”
我俩一听,更加高兴地想去参加打这一仗,可老马却给我们分配了另一个新任务,他说:“打起硬仗来,估计咱们自己也会有相当大的伤亡,因此伤兵转运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县委叫我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你们两个。”
赵洪则和我都了解这和打硬仗一样的重要,因此立即异口同声地答应着,把这项艰苦任务共同承担下来。
老马又说,根据军区的要求,三区的伤兵转运工作有两个重点,一个在甄家庄,一个在曹家坡。一分工,当然是洪则去甄家庄,我去曹家坡。
我说:“这一下,你们可以不用担心我的安全啦。”
赵洪则却一本正经地说:“尽管曹家坡离战场比较远,可鬼子的飞机这几天到处搜索,说不定还有些打散的溃兵藏在哪个山沟里,你还是要小心一些。”
马柏树连忙表示赞成,再三嘱咐我到了曹家坡要注意安全,转运站附近日夜都要放出岗哨。我听他们说得很有道理,马上说:“你们放心,为了对伤员负责,我一定会加倍注意保证安全的。”
老马和赵洪则齐声道:“好”!然后便一起把我送出了花子村,眼看我踏上了回曹家坡的大川,才转身去带领民兵奔赴甄家庄。
附注:花子村战斗是甄家庄歼灭战中的一场战斗。
本文作者黄其云为晋绥行署兴县第一任县长白认夫人,时任兴县三区干部。
黄其云简历:湖南长沙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于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曾任襄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南下入川,历任川西区农协会秘书长兼支部书记,西康省计委副秘书长、四川省计委办公室主任、中国作协党总支副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二秘、四川省文联副秘书长。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