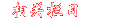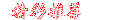
- 有这么一批《晋绥日报》的传承人(07月10日)
- 浇开中朝友谊之花(07月09日)
- 有一种记忆叫怀念……(07月08日)
- 有份爱心来自大唐(07月04日)
- 播撒慈善的种子(06月28日)
-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弘扬吕梁精神(06月21日)
- 悼念王军大哥(06月11日)
- “土窑泥坯”到军博(05月28日)
- 晋绥情怀和“智慧乡村”(05月23日)
- 2018年基金会工作回顾(二)(05月14日)
庚申忆逝(8—10)
发布日期:2016-01-26 15:09 来源:《庚申忆逝》 作者:晋绥基金会
八
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我离开南京回山西工作。临走前,我把工作向南京市筹委的同志作了交代,把家具都给了人。又把我的书装了两大网篮,上面放了一些鞋袜衣服,就上路了。那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控制得很严,路上带着书是很危险的。我从南京走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许多人都去送我,我穿得也很阔气,西装革履。因此,车警也不敢查我。到了徐州,就不行了,非查不可。我也不怕,处之泰然,用脚踢踢网篮叫他检查。他打开一看,全是鞋袜衣服,说谁要看你这些东西!让我把箱子打开,结果是什么也没查到,悻悻的走了。以后,就平安无事了。一直到了茅津渡,住了一夜,第二天雇了个骡子车,到了临汾,和王亦侠同志会齐,一起回到了西北安村。
从南京回到山西乡下来,是一种新的和上海、南京大不相同的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工作对象不同,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采取新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作为主要工作对象。同时,还要作县上、省里的上层人士工作,创造一个稳妥的隐蔽环境。
我回家不久,广惠渠发大水,从汾河引水的大渠决口了。这是一条引导汾河水冬灌土地的大干渠。通过蛛网状的大小支渠,平静而混浊的汾河水流进农田。冬灌一次有时可以淤积数寸厚的肥沃河泥,是一大水利设施,两岸农田得其利已经若干代了。往年发大水,广惠渠的水通过下游的磁窑河,瓦窑河能够顺利地流人汾河。这一年,下游的村子在广惠渠上拦腰筑了一条横渠拦洪,把广惠渠的千道堵住,大水一来,主流不通,越涨越高,渠道决口,高杆作物还不大要紧,矮秆作物就全淹了,大水眼看就要进村,群众很着急。当时村长张祝三是个靠摇货郎鼓卖布头起家的经营地主,人缘很不好,农民群众找他想办法,出主意,要求到下游刨渠放水,他不敢负责,转身逃走不敢回村。群众无奈,就到大庙撞钟,集合全村商讨办法,我也去了。大庙里,人们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谁也不敢作主到下游放水。有些人冲着我发脾气,说我念书识字,跑南闯北,做了大官,眼看水要进村,也不拿个主意,想个办法!当时,我感到很为难。自己是共产党员,眼看群众利益受到损失,那就太不像话。组织群众到下游刨渠放水吧,又牵扯下游村庄的利益,弄不好,要引起冲突,甚至动武伤人。我考虑再三,决定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我亲自到下游选了一个地势低洼,庄稼比较少的地点,决口放水,同时派人到下游村庄办交涉,说明利害,希望谅解。处在下游的村庄的人们,听说我是从南京回来的什么要人,还带着手枪,这样就取得了“谅解”,问题总算解决了。
这一炮打得很响,县上的人也很佩服,我就乘机做工作。因为我是反阎派,又是共产党员,阎锡山明今诵缉讨我,诉须浩点气氛。我把蔡元培给我的聘书放在手里,对外宣传我是回家养病的,又宣传我无意从政,专搞学问。这可起了大作用。远近亲朋都主动和我接近。文水中学的校长魏森林还请我去文水县中学教书。但我是来西北安村建立联络站的,不能离开,就婉言谢绝了。
就在这时,我的哥哥提出要和我分家。我刚回村时,家里人以为我在外面发了财,可以沾些光。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带回的东西,除了书以外,并没有多少钱。我回来后,经常客人不断,在家又吃又住,也引起哥嫂的不满,要和我分开过。我想这也好,我也需要一个单独的住处进行我的工作。我分得了一所院子,有五间房子。修理了一下,又栽了些树,弄得比较隐蔽。这样,就可以做联络站的地点了。
我翘首期待着北方局派人来和我联系。半年过去了,却是杏无音信。转眼就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这时西北安村选村长。其实,阎锡在山西搞选举,有名无实,不过借以骗人罢了。且不说穷人不可能当选,就是选上村长,也耽误不起那份功夫,最终还是有钱有势的当村长。然而,西北安村大开冷门,我居然全票当选。县政府看我虽无钱却有势,不仅在县上,在省城我也有许多认识的人。文水县的县长叫郭同文,霍县人,他老婆就是王亦侠的学生。就这样,顺水推舟批准我当了村长。这个差事,我虽说没兴趣,但是,却可以使自己有个合法的身份,便于今后的工作。因此,也就应承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是阎锡山的“黑村长”,真是可笑至极。我在西北安当村长时,另外还有两个副村长,我把财务、日常事务等都分配给他们两人去管,我自己专管修治广惠渠。我首先组织群众修渠,把渠坝修的又厚又坚固又整齐,并且和下游的村庄打通关系,共同商量把干渠修通,以便把水送到磁窑河,消除这个地区的水患。在修渠时,我又采取按土地的多少累进派工的办法,分配土方量。土地越多,出工越多,应完成的土方量越大,减轻贫下中农的负担。一些地富人家出不起工,只好花钱雇人顶替,这也使一些贫雇农得到了好处,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把干渠修通了。
这一年秋季又发大水,来势很猛,快要溢出大干渠。我日夜带着人在渠上守护,直到水位下降,我们才松了口气。白天就不派人守护了。一天中午,忽然听见钟响,上渠一看,原来是对岸交城县王家寨的人怕淹了他们的土地,竟把我们的渠坝扒了口子,大水猛冲进村来。村里的人气得眼都红了,要去王家寨打架,在对岸开口子,放水淹了王家寨。我认为打架扒口子放水,非出人命不可。我吼了一声:先堵坝后打架,保住村子再说。带领大家下水打坝堵口子,人多干劲又大,不到太阳落山,就把水口堵住,人们也累坏了。可是,大伙还吵吵嚷嚷,要去王家寨打架。我劝大家回村吃饭,吃完饭再去,把大家劝了回去。我又动员村公所杀羊打酒,让大伙吃喝一顿。完了,各人都跑回家里睡大觉去了。半夜,我故意派人去各户叫人,不但没有人出来,还遭受各户妻母的责骂。这样,一场武斗被制止,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接着就是和王家寨打官司,打了一年多,一直打到省建设厅。省建设厅派了专员下来调查,王家寨无理,打输了。为了给对方施加压力,慰问灾民,我又联系南岸五个村子,搞联合义演,演唱了五天大戏。我的宾客盈门,都是我出钱招待。本来这一时期,我在社会上也广交官员、士绅、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人物,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平日交友好客,就使我经济上渐渐拮据,五天大戏,吃喝招待,开销很大,终于把我分得的土地除了六亩多的祖茔地外,都典卖了。当了两年村长,把我的家产赔了个精光,一时传为奇谈。但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广泛了。交城县的公安局长白仙渊,浑源人,是我在太原农校的同学,要我介绍些人给他。我就把那些比较正直、会武术的小伙子给他介绍了不少,实际上也是安插我的人,抓枪杆子。我在西北安村一共呆了两年,至此,算是站稳了脚跟,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等待北方局组织来和我接关系,但始终没有等来,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朝思暮想,心急如焚,于是起了外出找党的念头。那时我的肺病又发作了,我对乡亲们说要到外地看病,实则是为了避免村里人继续选我为村长。于是便到北平去了。
九
一九三四年冬,为了和北方局取得联系,我又到了北平。住在宣武门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平办起了许多公寓,专供一些校外的游离学生、来往旅客们住。其特点是有许多小房间,一个房间住一个人,门口挂一个牌子,写着旅客的姓名。当时,北平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宪兵三团、便衣特务到处抓人,警车成天在街上呜呜叫。我在北平住下后,一面看病,一面找熟人打听北方局的下落。
一九三零年我在河北搞农村调查时,认识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韩德章等人。韩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天津《益世报》编副刊,叫“中国农村经济”,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韩德章知道我在西北安村当过村长,对农村隋况比较了解。就约我为《益世报》副刊写文章。我刚到北平,生活无着落,当下也难找到北方局,就答应了。把我在山西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以张稼夫的名字,发表在《益世报》的副刊上。我用张稼夫的字公开发表文章,意在找党,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以后薛品轩来看我。关于薛品轩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们一起在上海社会研究所工作时,就很了解他。此人为人正派,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也了解我们党的一些活动,有时还为党作事,但是当时没有入党的要求。他被解聘以后,通过关系回到北平,在北平法商学院学学习,他看见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张稼夫三个字,大吃一惊。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大胆,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正在找你,你还敢把名字写在门口。”接着,他告诉我,张西涛被捕,石凯福后来也被捕了。石凯福被捕后写了脱党声明,表示不革命了。他让我赶快把门口的牌子摘掉,重写了一个假名字,又劝我另搬一个地方住。我问他,石凯福现在在哪里?他说,石凯福出狱后,觉得没脸见人,隐名埋姓,不知哪里去了。我又把来北平找北方局的事告诉他,他说愿意帮忙,劝我不要着急。后来,我和北方局接上关系,他起了重要作用。薛品轩走了以后,我就从公寓搬了出来,后来根据薛品轩的建议,搬到北大农学院附近的罗道庄一个小小的农村公寓住下。一边养病,一边打听北方局的下落,有时也到城里看望朋友。同时也给报纸、刊物写点文章,以维持生活。《动乱前夕的山西政治与农村》,就是应薛暮桥同志之约,在此时写作,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的,署名悲笳。这些文章都是以我在文水县西北安村当村长时收集的材料为基础写作的,其内容也都是以山西农民的悲惨生活事例,揭露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以及农民的反抗斗争。
一九三五年夏,当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奔向抗日前线的时候,蒋介石在华北加紧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允许日本进驻滦东非军事区,唆使殷汝耕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媚日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首先,在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大中小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运动波及全国。我也投入了这一运动,参加了示威。也就是在这一运动中,我认识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如:北大的徐荧均,是徐燮均的弟弟,他是北大地下党支部的成员。又如,法商学院的地下党支部成员姜玉荷,后来改名姜珊,她和薛品轩的关系很好,后来到了一二零师的三五九旅,现在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工作。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也很同情我,但都无法找到北方局,无能为力。后来,经过薛品轩的介绍,我结识了张路一,他从薛品轩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对我很亲近。有一天,他领来一个小青年,这个青年人连童声还没变。张路一说,他叫张骁,他可以帮忙为我给北方局送信,我自己心里有点顾虑重重,可是,除此而外,别无他法。最后,我还是写了个报告,叮咛再三,把报告交给了小张骁。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直到前年,我在科学院见到一个名叫张文松的同志,觉得此人很面熟,我通过人事部门一查原来他就是帮我送报告的张骁。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送报告的事,他说为了送那个报告,还受了批评。就在张骁把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拿走以后不久,北方局一个姓李的同志托人转告我,说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收到了。经调查研究,认为报告是可信的,同时对我在文水县的工作表示赞扬。但又说,北方局至今没有收到过上海党组织转来的关系,待查明以后通知我,要我安心养病,至于工作问题,待以后安排。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的事了。
不久,我得到了红军在山西渡河东征的消息,并且看到了“东征宣言”。接着又得知,红军已经占领了晋西地区,先锋部队南到侯马,北达晋祠。这消息使我兴奋不已,红军已经到达我的家乡,我还坐在北平干什么,于是我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山西。
十
我从北平回山西的打算,是想和红军接触,尽我的力量做一些工作。待我回到山西,红军已完成任务,发出回师通电,撤回黄河西岸去了。听说汾阳、孝义城里还能看到红军张贴的抗日标语,也能听到有关红军的传闻,如红军在文水县开栅镇打了大地主杜凝瑞家的土豪等,但却不见红军的踪影。于是,我就到了太原,住在大南门铁匠巷的文水会馆里。随后,通过赵青誉介绍,到了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暂时有了个立足之地。
红军东渡时,阎锡山惊恐万状,红军回师以后,阎锡山便掀起了白色恶浪。在太原和各县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如国民师范的四名青年就是在这时被杀害的,甚至普通老百姓也深受其害,只要被认为是可疑者,均被刑讯,甚至虐杀。在太原市,任意搜查民房,无端检查邮件,在书店没收、焚烧进步书刊,没收货物,查封商店。这一时期的山西,城市里百业萧条,乡村是路断人稀,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但是阎锡山的暴行,压不住群众的愤怒,革命的烈火终究是会燃烧起来的。
我到太原不久,北方局派李宝森同志来太原,负责恢复中共山西省工委,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他是山西清源县人,过去曾在山西大学读书。他爱人是太原城内大丰客栈老板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李宝森同志到达太原后,托郭森宇给我捎来一张条子,说要找我。这样我们就约定的时间会了面,接上了我的组织关系。
我长期在南方工作,对于山西党组织的情况,只听过一些传闻,并不了解内情。这次回到太原,才了解一些情况。据了解,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阎锡山宪警特务统治和残酷镇压,以及山西党组织受“左”的影响,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轻敌,所以屡遭破坏。不少优秀党员被捕被杀,有的被迫离开山西,开展工作相当困难。我还记得,早在一九二七年夏,山西省委书记王瀛同志到武汉党中央汇报工作,离武汉回山西前,曹汝谦同志在汉口晋阳楼饭庄为他们夫妇设宴饯行的情形,我和王亦侠同志作陪,那时王瀛同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是刚回山西,即被捕杀。此后,党组织一再进行恢复工作,又一再遭受破坏,可见阎锡山手段之凶狠。不过阎锡山所采取的是比较隐蔽的先打进来然后一网打尽的做法,或假借种种名义加以暗杀或拘捕,关进监牢、训导院或反省院(中央系),很少用公开屠杀和枪决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阎锡山不仅对共产党如此,就是对于蒋系国民党系统的CC和复兴社也是一样,均使其无法在山西境内存在。红军东渡回师之后,尽管阎锡山加强了镇压,革命力量仍是有增无减。我党的抗日主张经过我军东征宣传,就更加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党的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工作搞得比较扎实。李宝森同志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恢复了山西省工委。由李宝森同志任书记,武永祥同志任组织部长。武永祥同志是平遥县人,曾在太原师范读书,他以“新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未离开过太原,也保护了一批党的骨干力量,并保持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山西工委的工作,开始主要是依靠了武永祥同志保存的骨干力量。工委的宣传部长是赵仲池同志,我是文教委员,负责和新闻、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当时,和我有联系的有亚马、卢梦等人。卢梦现在北京文艺界工作,他是我介绍入党的。刘子超、温建功、宋维静、朱宝善等人也是我联系。由外地回到山西来的人也由我负责联系,如雷任民同志,他于一九三六年回来以后,就是由我接转关系的。后来,为了加强文化界的工作,又办了个中外书店,推销一些革命书籍,建立了一个文化界接头的地点。
十月,北方局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张友清同志来山西主持省工委的工作。张友清同志是陕北神木县人,是我党的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年轻时曾在太原第一中学读书,和郝广盛同志在北京中国大学入党,曾在黄埔武汉军分校学习,李光军是他的好朋友,那时他们于礼拜日常到我家中来聚会。郝广盛同志在反击夏斗寅时牺牲了。张友清原名张学静,是被送到安徽毫县杨虎臣部工作的,随后长期担任地方党的领导工作,曾担任过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和张友清同志一起先后来山西的还有徐子荣同志和赵振声(即李葆华同志)。他们来太原后,张友清同志就住在胡西安家里,胡西安是共产党员,和阎锡山有点亲戚关系,住在他家不但保险,还便于了解官方情况。赵振声同志住在武永祥家里。那时,我住在太原南新街,徐子荣同志住在我家。我是个穷教员,不大为人注目,工作倒也方便。住在我家的还有省工委的秘书,名叫张永青,榆次县人对外他就叫我表哥,叫王亦侠表嫂,当时王亦侠负责太原纱厂和纸烟厂的女工工作。我们和张永青同志处得很好,至今他还叫我们老俩口表哥表嫂,改不过口来。
张友清主持山西工委工作以后,李宝森同志调离,又增加了徐子荣同志为工委秘书长,赵振声同志任工委组织部长,武永祥同志任组织部副部长,其他人事没有变动。恢复省工委以后,又恢复了太原市委,赵林同志任书记。市委主要任务是在厂矿和学校开展群众工作。当时山西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内蒙,正向绥远进犯,危及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于一九三六年的十月间进行了“绥东抗战”。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周小舟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太原。紧接着,中央又派彭雪枫同志到太原工作,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对阎锡山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上层的和基层的关系,特别是群众运动,促使阎锡山的防共反共政策有所收敛,在推动阎锡山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成效是显著的。
在张友清同志来太原之前不久,薄一波同志接受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太原,和阎锡山搞统战关系,晓以大义,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接着,北方局决定成立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同志负责,开展对阎锡山上层人士的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领导,不和山西工委发生联系。当时,太原还有一个由王世英同志负责的特科系统,主要任务是搞情报工作,也不和山西工委发生联系。这三个系统各自为战,统一由北方局领导,工作成效非常显著。阎锡山在我党的统战工作推动下,又迫于形势,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开始向抗日联合方面转化。九月,宋邵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同志发起筹备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由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负责领导,并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调进牺盟会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其中有杨献珍、周仲英、韩均、董天知、廖鲁言、李力果、冯基平、徐荣等同志。这样,就充分发挥了这个群众组织的作用,放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促使山西抗日的形势,迅速走向高潮,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
营救工作也是当时的一大任务。那时在山西关押着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其中包括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王若飞同志。开始,阎锡山不承认太原监狱中有王若飞同志,经省工委和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十六人工作委员会的调查并和王若飞同志取得了联系以后,向阎锡山提出证据。他才不得不释放王若飞同志。接着在第一监狱、陆军监狱关押的一大批政治犯经党组织的营救,也相继先后获释。另外,阎锡山还办了个训导院。在这个训导院里,除了关押着一批政治犯,还关押着在红军东渡时俘虏的一部分红军小战士和伤病员,企图从精神上征服这批红军战士。训导院的院长是赵戴文,他是阎锡山的老师,山西省主席。院主任是叛徒郭挺乙,实际负责人是教导主任时逸之和教导员郭实甫,这两人是共产党员。后来,在这里被关押的红军战士和其他政治犯全部被营救出来,由我们党接收送往各地、县担任领导工作或者到军政训练班,学习结业之后,编入敢死队,这批同志和战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党中央根据山西出现的新局面,从全国各地派来了许多优秀党员干部,并发动大批大批的革命青年到山西,参加抗日行列。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工作是通过牺盟会进行的。牺盟会有一套组织系统,薄一波同志是总领导,总部设有组织(由薄一波同志兼管)、宣传(由裴丽生同志负责)、总务(由戎子和同志负责)等部门,办有《牺牲救国》周报。各地设有牺盟中心区,各县有牺盟特派员,会员是公开身份,遍布各地,影响全省。省工委的同志也戴一枚牺盟会的徽章,以作掩护。而大街上的摊贩、车夫也以佩戴此徽章为荣。牺盟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到底有多少会员也说不清,佩戴徽章的自认为是会员。我受省工委的指示,也参加牺盟会召开的各种会议,还给《牺牲救国报》写文章。牺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宋邵文同志分管宣传委员会,牺盟会的章程、计划等大都是他起草的。这个委员会中和我经常接触的有裴丽生、赵石宾和侯振亚等同志。
当时,我还另有一个任务,就是省工委指示我到民众教育馆工作,占领这个宣传阵地,还给我派了两位助手。一个是常芝青同志,交城人,中共党员,搞文字宣传工作。一个是搞美术的,名字记不清了,这个同志后来到了延安鲁艺学习。这个民众教育馆名义上是官办的,实际上成了我们党的宣传阵地,出壁报,印宣传画,散传单,闹个热火朝天,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在元宵节那天,由牺盟会发起,太原市举行提灯游行,宣传抗日。街上到处是耍龙灯,踩高跷,划旱船的游行队伍,每支队伍都有宣传抗日内容的节目,旗帜、灯笼上写的也是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当天晚上举行各种报告大会,主题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十分红火热闹。太原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向前发展,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前,省工委通过牺盟会等组织办起了各种训练班,如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士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等。这些训练组织都是以阎锡山的合法名义搞起来的,大部是我们党派人主持工作,受训的也大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这样就从组织上为抗日战争作了准备。当时,党的领导是完全合乎山西实际的,是非常英明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不久,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杨尚昆、彭真等同志来到太原,接着周恩来同志、彭德怀、肖克等同志也到达太原。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到来,使太原的抗日群众运动又出现了高潮。此后,为了加强省工委的工作,北方局派林枫同志为省工委副书记,协助身伴侣病的张友清同志的工作。十月间,将我们这个要随同阎锡山总部一起行动的党委改组为中共山西省委,省委设立了军事部,从一一五师调来习来黄骅同志为部长。黄骅同志是湘鄂赣根据地的老同志,人很精干,军事上很有经验,在他负责军事部工作期间,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太原失守前大约两个星期,林枫、张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徐子荣同志到冀鲁豫工作,由我担任秘书长。又说,根据形势的需要,省委一分为四,赵仲池同志调晋西北工作,赵振声同志调到晋东北工作,徐子荣同志调冀鲁豫工作,我们随阎锡山的总部南下。阎锡山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以便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同时,为了和阎锡山易山总部的称呼相对称,其他地区党组织叫党委或工委,只有我们叫省委,实际上是各自为战。林枫和张友清同志还告诉我,阎锡山的总部要搬临汾,要我去打前站,给省委找房子。我接受了任务,立即动身,到临汾去了。
张稼夫 述
束为 黄征整理
(本站编辑:左丽)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